学术资讯丨我系郭峻赫教授出版新作《马基雅维利政治哲学导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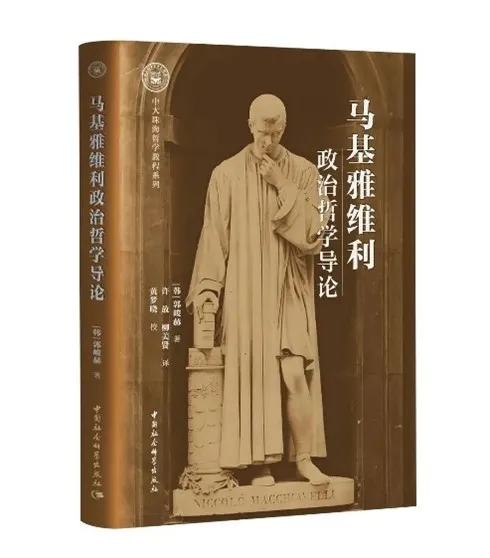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郭峻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逸仙学者、博士生导师。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曾先后任职于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研究领域是西方政治哲学、当代政治理论和比较哲学。特别关注但不限于从古典共和主义资源中构建“相互非支配”的调节性原则,以引导处于冲突和紧张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审议。近来致力于探讨儒家思想是否需要重构以应对当前社会政治和全球正义的问题,相关发表包括“个体性和关系性”(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023),“儒家对基督教之爱的重新评价”(Religions, 2023),“儒家的角色伦理学与非支配”(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2022),“非自我中心主义的全球正义”(Dao, 2021)、《东北亚语境中的现代性》(Routledge, 2023)以及《马基雅维利和共和主义的领导力》(Routledge, 2025, 即将出版)等。目前担任劳特利奇“东亚语境中的政治理论”系列丛书主编、国际英文期刊《社会和政治哲学》编委。
作者自序
自序: 拥有梦想的现实主义
一 拥有希望的现实主义
马基雅维利不知道后来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嘲笑过那些所谓高贵哲学家的伪善。他既不想用令世人尊敬的道德标准来炫耀自的哲学,也不想把不受世人欢迎的自己美化成孤独的哲学家。他只是想通过列举那些“德行”不得已成为“恶行”的事例,来重新思考道德标准,同时否定并排斥那些能够使自己成为哲学家的一切形而上学要素。他把此前哲学家们的全部政治教诲都称为“错误的想象”(falsa immaginazione)。
马基雅维利排斥形而上学的最大原因,是当时统治阶层的腐败。欧洲局势的巨变已经威胁到了佛罗伦萨的生存,而贵族们依然只关注自己的利益,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甚至可以给外敌大开方便之门。知识分子们虽然对政治现实极其失望,却只用哲学反思来消除自己的挫折感。这所有的一切都让公民们感到绝望。也就是说,他对形而上学的敌对态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苦痛,因为人们关于道德与哲学的谈论,已经沦落为试图通过维持现状来获得利益的政治修辞。
因此,马基雅维利重拾忘却已久的梦想。他梦想着公民重获自由,意大利从列强的魔爪中挣脱出来:梦想着小小的城市国家-佛罗伦萨能够像罗马共和国一样成长为帝国,进而主导时代的变化。当所有人都认为君主政体能够克服佛罗伦萨的混乱与孱弱时,马基雅维利却指出,与安静的威尼斯相比,有必要把喧嚣骚乱的罗马作为理想目标。他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建立共和国需要“一个”(uno solo)卓越的人物,但也在思考如何唤醒公民“不想受他人支配”的欲求,实现公民自由。
可惜,没有一个人认为马基雅维利能够实现这个梦想。世人指责他,给他贴上“理想主义者”的标签。就连他的密友圭恰迪尼(Francesco Guicciardini)也参与其中。圭恰迪尼认为他过于信赖人民,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罗马,与西塞罗梦想的以元老院为中心的罗马共和国典范相去甚远。 实际上,马基雅维利并没有无条件地相信人民。他强调,集体理性发挥积极作用也是需要条件的,并且他也关注那种能够阻止共和国向支配和从属倒退的领袖能力。但圭恰迪尼所说的依靠“贵族”或“少数人”的共和国,从来不是马基雅维利所希望的。
严格地讲,马基雅维利似乎认为,当时的名门子弟和权势贵族还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就像西塞罗认为格拉古兄弟的改革悖逆了时代发展的潮流,马基雅维利时代的贵族也试图维持以元老院为中心的贵族统治,妄图倒转“人民”成为国家力量的历史车轮。在《君主论》和《用兵之道》中,马基雅维利叹息道,掌权者倚重雇佣兵,忽视了“人民”比“军队”更重要的事实。在《李维史论》和《佛罗伦萨史》中,马基雅维利对那些拿人民的无知作为借口来满足自己私欲的贵族,表达了他的绝望之情。他批评道,这些人的“现实主义”是没有希望的现实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残酷的表现。
二 不能成为约伯的文艺复兴人
即便如此,马基雅维利也没有用支配当时战略家头脑的反理性主义来武装自己。虽然他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回到人文主义传统的浪子、掌权者眼里的外邦人,但他没有抛弃自己从古典和历史中学到的智慧。他自信地认为自己的想法是通过古典和经验形成的,称自己的知识为“关于历史的真正知识”(vera cognizione delle storie)。
马基雅维利所说的知识,意味着对罗马教会的基督教历史观的挑战。事实上,他在《李维史论》中说罗马教会的教育存在问题,只不过是他的一个委婉说法。罗马教会与世俗政权毫无二致,为生存而展开斗争,神职人员的腐败让公民感到厌恶,就连辅佐教皇的圭恰迪尼也承认,如果不是职责所限,“我会像爱我自己一样,去爱马丁·路德”。因此,如果马基雅维利仅仅满足于这种程度的批判,他所说的“前人未到”之地不过是个夸张的修辞。
马基雅维利的意图体现在他使用的“历史”(storie)一词中。他没有使用“历史”的单数形式,而是使用了复数形式,这当然是有意
为之。基督徒认为历史是神的旨意得到贯彻、启示得到实现的过程,是奔向终结的时间的延续。马基雅维利对此不以为然,对于他来说,历史并不朝着一个固定方向发展,不是独立于人类意图的某种意志施加影响的结果。他将历史理解为人类大大小小的日常生活,喜悦与绝望的英雄行动,欲求和激情引发的社会政治事件。并且认为,只有通过这些事情,人类才能真正拓展“知”(eidenai)的领域。
因此,马基雅维利无法像《圣经》里的约伯那样等待上帝的恩典。他不能接受约伯的态度-在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况下,由于未知的原因,接受上帝的残酷刑罚,一边忍耐一边等待上帝的帮助。从这个思路来看,马基雅维利经常提到的“等待上帝的恩典”不过是他强调自己处境艰难的修辞手法。就算他拥有信仰,也和当时欧洲大部分人--在今天忏悔,明天犯罪,然后再忏悔的日常生活中,向上帝祈求幸福的文艺复兴人--起伏不定的心态大同小异。
在这个背景下,“神”(Dio)在马基雅维利这里,不得不与希腊罗马人相信的“命运女神”(Fortuna)、占星术士口中的“天”(cie- lo),一同竞争人类世界的主导权。对于当时的意大利人来说,世界“虽然是由上帝创造的,但是天和命运女神主宰着人间诸事”。马基雅维利的想法则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惯常观念。所有的神都会介入人间事务,基督教全知全能的上帝只是众神之一。并且,所有的神都是胜利者的朋友,对失败者则无比残酷。
马基雅维利的历史观完全冲破了基督教的藩篱。它包含了一种人性的两难挣扎,一方面,接受变幻莫测的“命运女神”安排的、充满玩笑又无法预知的未来;另一方面,又拒绝将自己的一切托付给神。如果说前者让政治家在思想的多样性和激烈对立中重新认识政治的可能性,那么后者就让我们感受到文艺复兴哲学家想要拯救堕入深渊的公民生活的苦恼。他指出:“分歧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能够得到很好的制度化,就可以同时带来公民的自由和国家的强大。”他坚信,意大利的解放永远不可能通过萨伏那洛拉那种先知(cantastorie)所高喊的“恢复信仰”来实现。
也许正因为如此,马基雅维利甚至不关心灵魂(anima)的救赎。相比“与上帝交谈”的萨伏那洛拉的说教,马基雅维利宁愿倾听“与精灵相遇”的奴玛(Numa)的谎言。如果有可能的话,就应该为政治目的而利用宗教,如果是为了公民的自由,就没有选择的余地。如果在抉择的瞬间犹豫不决,地狱就等在面前。正如马基雅维利讽刺那位把共和国交给美第奇家族并仓皇逃跑的皮耶罗·索德里尼(Piero Soderini),说这种拥有“可笑灵魂”(animasciocca)的政治家,在地狱也不会受欢迎。对于极富颠覆性的马基雅维利来说,与其愚蠢地忍受时代的苦痛,不如抱着下地狱的决心奋力一搏,也许这样会显得更加善良一些。
三 “可能性”美学中的新政治
马基雅维利梦想着人类通过结合“哲学反思”与“诗的可能性”成为历史主人公的时代能够到来。这看上去像是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一把哲学和诗、对永恒的探求和对未来的想象融为一体。但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马基雅维利并没有像亚里士多德那样,希望通过哲学反思来证明“好生活”(eu zen)和“德性”(arete)之间的关系。他既不想让政治家的德性--“审慎”被“节制”这一道德主题禁锢起来,也不想追求永恒的哲学思考。他只不过将亚里士多德对诗人的期望,转移到了政治家的身上。他告诫人们,应该超越经验与现象的束缚,去想象和构思未来。
马基雅维利的忠告主要由两条主线构成。第一,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罗马共和国。当时的知识分子们对罗马共和国的想象是建立在西塞罗的著述之上的。他们所梦想的是早期的罗马共和国,即公民自由与元老院审议形成良性互动,各阶层之间和谐共存。因此,他们更向往贵族支配的、封闭的威尼斯,而非因贵族与人民的政治斗争而陷入混乱的后期罗马共和国。他们虽然羡慕罗马帝国的光荣与和平,但却追求早期罗马共和国小型城邦的梦想。
马基雅维利认为,这些知识分子梦想的罗马共和国是“贪小失大”的产物。一方面,他批判道,知识分子对贵族和权势家族宣传说,公民自由只会加剧国内的分裂和混乱,使他们露出了自己的真实面目;另一方面,他感叹道,知识分子出于对人民参与政治的习惯性反感,无法认识时代的变化。他指出,如果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不要说早期罗马共和国,就连恺撒之类僭主的登场也只能以国家危机的名义予以容忍。马基雅维利的论述就像一个暂停键,试图打住人们从15世纪开始的“君主政体”的讨论,让人们对似乎即将消失于16世纪的“共和国”又重新燃起了希望。
马基雅维利眼里的罗马共和国是以“分歧”而非“和谐”为基础的。人民擦亮眼睛保持警觉,牵制贵族的专横和权力腐败;贵族则放下他们自己的关系和背景,为获得人民的支持而互相竞争。格拉古兄弟改革暴露出的早期罗马共和国的矛盾表明,以元老院为中心的“贵族”审议需要被更广泛的人民政治参与形成的“民主”审议所取代。此外,人们不仅应该容忍制度内部的分歧,还应该容忍那些可能改变现有制度结构的分歧,政治家应该在人们的分歧和对立中,通过实现人民“不受支配”的消极欲求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不仅如此,马基雅维利还展望了“公民自由”与“帝国扩张”之间的关系,这是其他人从来都不敢想象的。
第二,最大限度地发挥那些怀有政治野心的人们的激情。马基雅维利是那个时代修辞学的代表人物。他没有强大的家族背景,年纪轻轻就成为第二秘书厅的秘书长,在索德里尼执掌的共和政府中负责几乎所有外交文书的撰写,在佛罗伦萨获得“神赐文笔”(divinaprosa)的评价,这所有的一切都与他的文学才华息息相关。他希望用自己卓越的修辞技巧去说服那些能够为意大利解放而献身的“潜在僭主”。对于当权者,希望他们不要墨守成规,勇敢地开拓新的政治前景;对于未来的领导者,告诉他们只有实现公民自由,才能获得真正的光荣。
在这个过程中,马基雅维利甚至否定了“命运女神”。他认同并享受着政治的可能性与未来的不确定性。但是,他生活在一个,相比顺应潮流(tempi)的狐狸般奸诈,更需要狮子般勇猛的时代。因此,他提出了一个应对方案,就是用最能实现可能性的“勇敢”(auda-cia)来代替用节制调和过的“德性”(arete)。因为,他认为,上帝赐予的自由意志(liberoarbitrio)、“命运”(fortuna)和“德行”(virtù) 哪怕得到绝妙的组合,也无法立刻引发行动。马基雅维利比任何人都要清楚,这个时代需要一个不接受意大利的悲剧宿命,用意志压制命运女神的人。
最终,马基雅维利与苏格拉底开启的哲学传统彻底决裂。他将“非支配”作为目标,而非致力于“好生活”;他穿梭于事实与虚构之间,毫无顾忌地使用助长政治野心的修辞,把扩张成帝国的罗马共和国作为政治理想,而非自治城市。这样的试验,不论他是否有意,都发展成为现代人想要克服“自然”(Nature)限制的愿望。并且,他大胆果断地对人类能力无法企及的领域表示漠不关心,结果促成了一种由“生存本能”和“权力欲望”结合而成的人类“激情”的现代解决方案。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感谢马基雅维利没有把“道德”作为献身于变革的理由。通过萨伏那洛拉的没落,他清楚地知道政治理想与道德要求的结合带来的不是普遍正义的实现,而是持续的恐怖与暴力。因此,他的“权力政治”(Machitpolitik)是以对人性弱点的理解为基础的,他的“结果主义”是以实现“非支配”--而非“支配”--这个消极欲求为尺度的。就好像已经预见到了革命时代和法西斯主义带来的悲剧图景,他试图通过生活叙事,而非政治理念,将自己的想法融入政治中。
四 新的梦想
马基雅维利认为当时佛罗伦萨的绝望状况是“贵族的懒惰”与“民众派的鲁莽”共同造成的。贵族担心“失去自己拥有的东西”,再次陷入没落,而民众派则以“改变一切”的极端思维将人民的生活引向深渊。因此,他首先构想的制度是,通过公民自由制约贵族,让那些试图通过煽动而获得权力的人们的野心无法得逞。
但是,马基雅维利非常清楚,这样的制度构想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同时他也很清楚,如果承认这个观点,就会让当时的知识分子沾染失败主义者(defeatist)的不良习气。因此,他努力给贵族描绘“新的梦想”,给民众派的政客勾画“生活的面貌”。他希望沉迷于自我利益的贵族能够觉醒,为扩大公民自由和领土而奋斗;他希望大众政客(popolari)不要关注那些脱离现实世界的“妄想”,而应关注“我的孩子,我的家人”的日常生活。他确信,只要保守群体能够拥有梦想,进步群体能够着眼现实,就可以创造出把绝望变成希望的机会。
当然,马基雅维利的所有想法并不是都可以根据佛罗伦萨面临的时代要求得以正当化的。特别是,他强调的帝国主义扩张与他倡导的“非支配”之间有着无法消除的紧张关系。他虽然可以就“邪恶导师”的指责进行自我辩护,但是无法回避这样的批评,即他使爱国主义沦落为集体利己主义。虽然一些人关于道德的谈论沦为维持既得利益的修辞,但是在国际关系的残酷现实中,古典共和主义者为了贯彻“非支配”而进行的努力也并非完全无益。
即便如此,人们也没有必要按照现代人的需要歪曲解读马基雅维利的著述。相反,有必要冷静地思考其主张的深意,并从多个角度进行探讨。他对人类欲望的洞察、对政治权力的审美视角、其制度构想中的审慎以及颠覆性的想象力,这一切都应该按照马基雅维利本来呈现的方式来进行探讨。通过这样的过程,人们可以发现,他关于“多数者”的观念、关于帝国的构想,都可以归结为着眼于“非支配”的实现。
虽然笔者才疏学浅,但仍然希望通过这本书,让马基雅维利那些被其各种“面孔”掩盖的政治哲学能够得到更加深入而广泛的讨论。
郭峻赫
2024年1月
中山大学珠海校区
本书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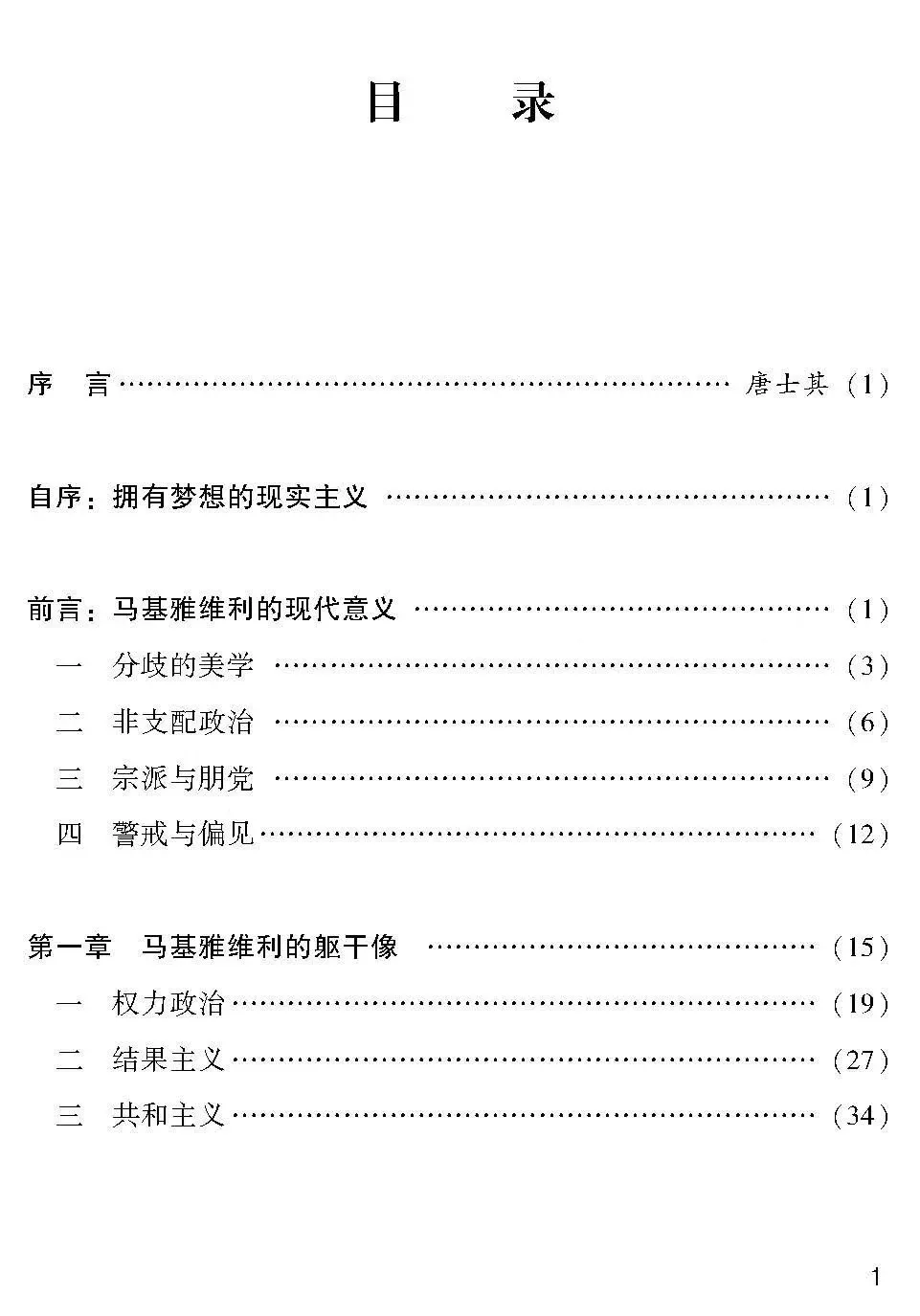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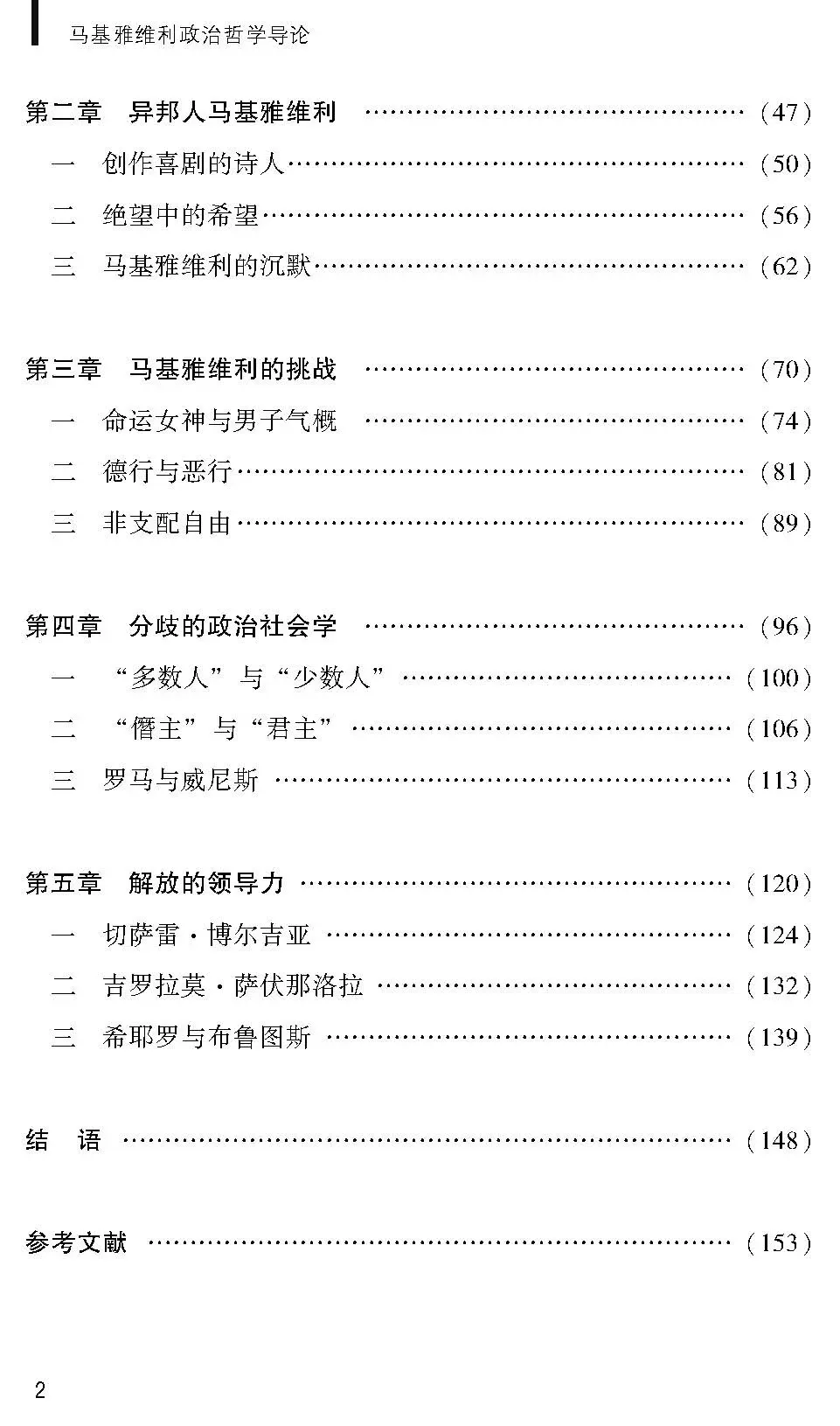
来源|哲珠新媒体
编辑|周泳洋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