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资讯|我系秦际明副教授出版教材:《论语广义》
我系秦际明副教授出版教材:
《论语广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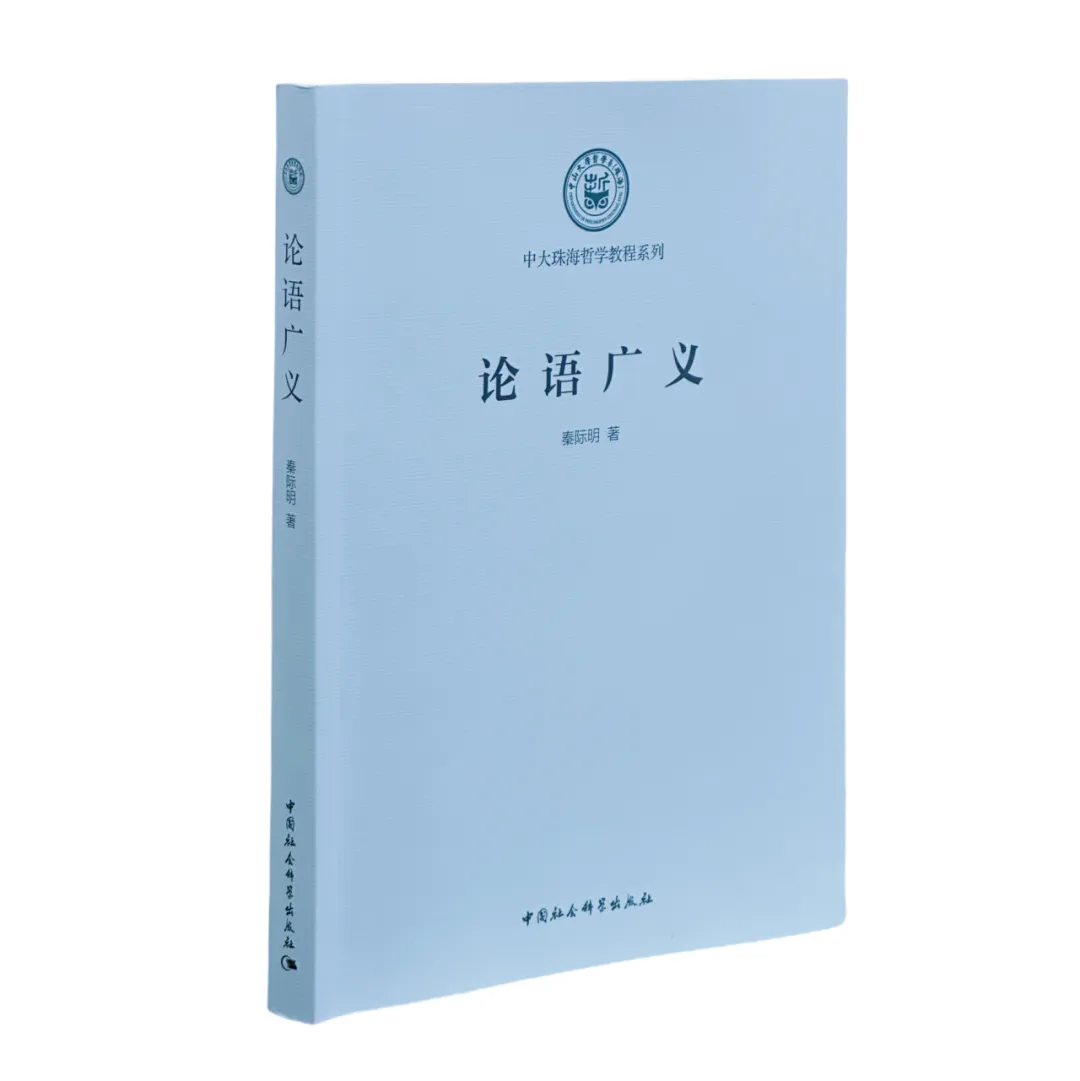
编者按
中山大学着力推动教材建设,近年来培育了一批优秀教材。本栏目旨在展示我校教师在教材建设上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以期推动广大教师用心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
作者简介

秦际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2部(待出版学术专著2部),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1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后期资助项目,其他省部级项目3项,及中山大学教材、教学建设项目2项,并获得中山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团队)。研究方向为经学、中国政治哲学与中西哲学比较。
教材简介
本书是对《论语》文本的拓展性诠释著作。《论语》以其深刻的思想较为全面的塑造了中国传统社会,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有极为广泛的影响。而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时代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论语》所刻画的社会运作逻辑是否仍然起作用?本书在传统《论语》注疏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科学,运用《论语》的思想来讨论社会生活中的诸多主题,因而名之为“广义”。本书作为讲稿在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本科生课程《儒家经典选读》及《中国哲学经典》(人物、著作与问题)等课程中讲习数年,后在讲稿的基础上拓展成书。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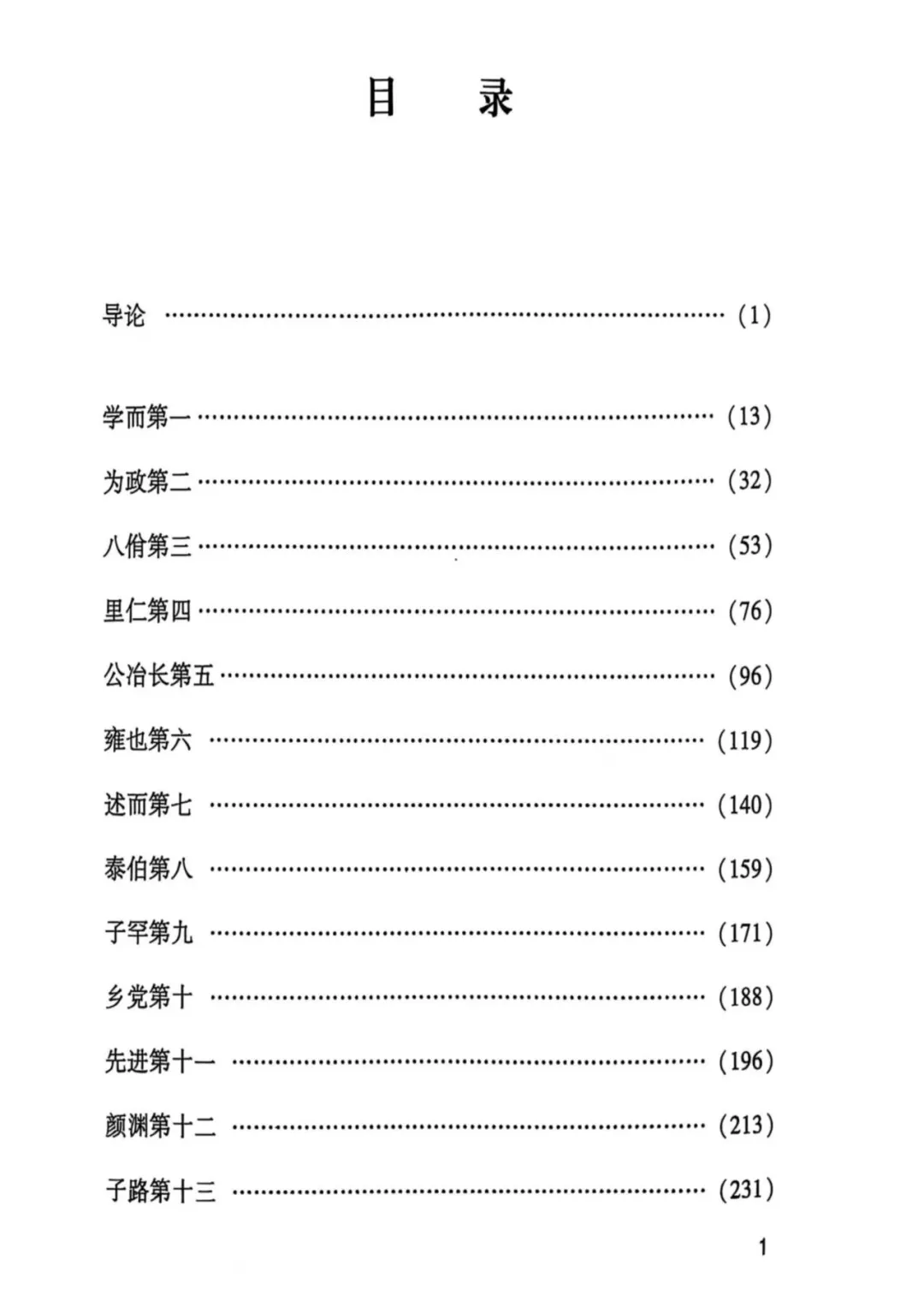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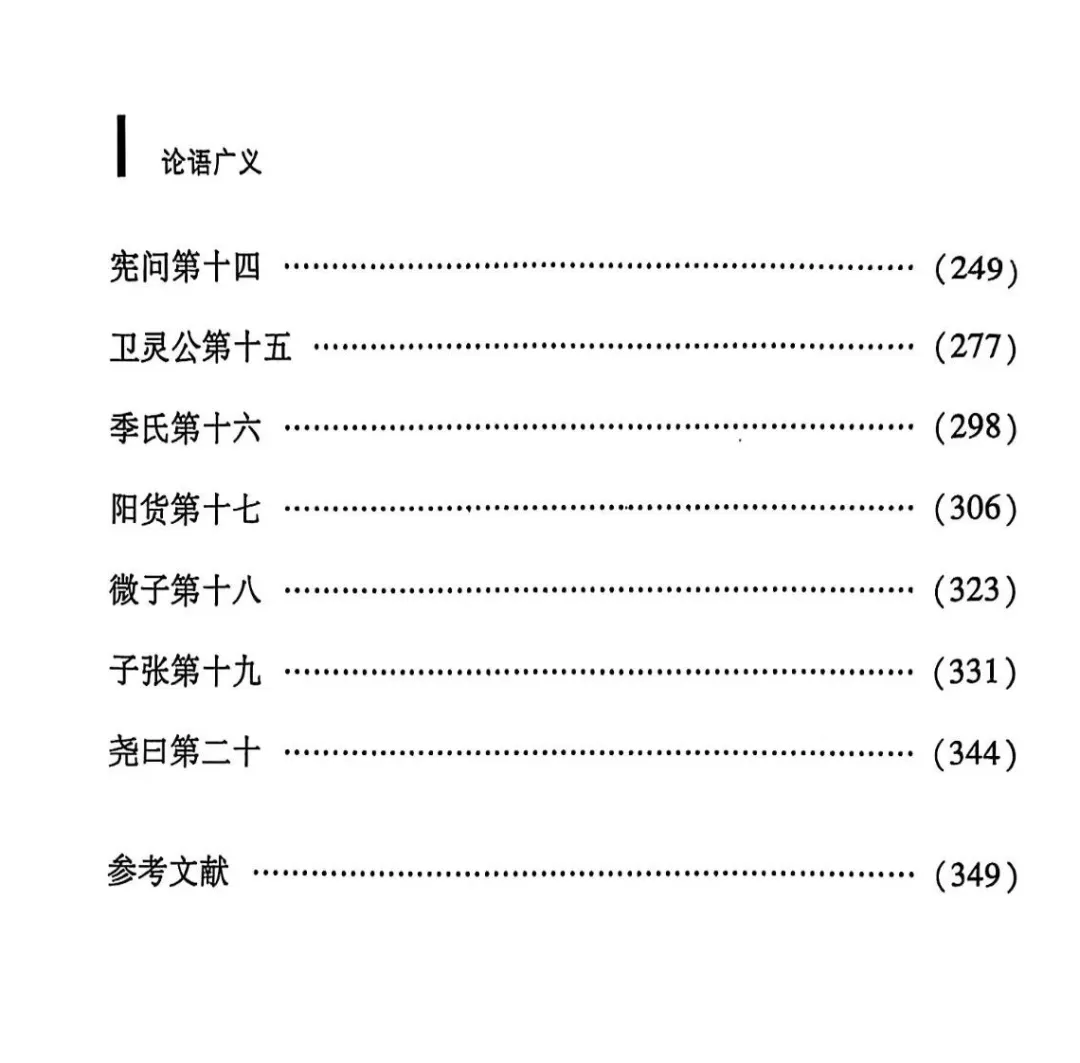
导论
随着时代变迁,如何理解儒家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其难点在于,如何提炼儒家的主要思想及其思维方式来思考时代问题。在教学实践中,我们发现许多学生难以在中国古代典籍的学习中找到问题意识,不能作专题化的深入思考,这非常不利于人才培养。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儒家典籍不是专题式的论文,需要读者自己去归纳其思想主旨,以形成关于儒家的知识系统。另一个原因是,古代儒家的思想言说针对的是古代社会问题,而现代社会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以及现代学术的话语系统、思想方法及问题意识,都与古代儒家差异巨大,如何将古代儒家的思想与现代学术对接起来,这也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此,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中解读《论语》需要回应现代社会问题,也需要回应现代学术中与之相关的思想主张与问题。故而有必要结合当前的儒家文化教学实践和时代问题来重新编撰一本《论语》阅读指南,以帮助学习者更好地理解《论语》的思想世界及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
深入理解儒家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理解儒家与中国古代社会及现代社会的关系。反过来,要理解这组关系,又须以深入理解儒家为前提。这就构成了解释的循环,不过,在当前多元的文化思想环境下,我们更应先理解儒家与现代社会的关系。孔子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是以正名为先,而后知学。
一、儒家的现代诠释问题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中国战败,引起了很多学者对中国失败原因的反思,一些学者认为是中国伦理与文化导致了中国社会的诸多弊病,由此引发对儒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如果考察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期的世界史,我们会发现,在西方文明的强大冲击下,文化选择是后发展国家所面临的普遍问题,如日本、土耳其、伊朗、印度、泰国等,我国也不例外。这些后发展国家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刺激下,一般会产生三种文化主张,即文化保守派、全盘西化派与文化调和派。不少国家的文化发展经历了从西化派到保守派的更替,如土耳其与伊朗。三派并存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文化现状,我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大致也是如此。只是,清末民初反传统思潮中所形成的学术话语对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影响极为深远,远非文化保守派与调和派可比。中国现代学术对儒家的理解与诠释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近现代以来儒家思想现代诠释的第一个主题是基于现代价值观念对儒家伦理的批判,将儒家的三纲五常塑造为现代价值观念的对立面。这里面的理论问题其实非常复杂,如果我们深入考察汉代人所持的三纲之说,就会发现,三纲的核心是一种道义,而这种道义恰恰是人格的挺立,而非人格的屈从。换言之,儒家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有差异,但并非对立。遗憾的是,晚清民初的一些学者过于仓促地将中西文化对立起来了,形成了反传统的思潮及其话语体系,影响至今。
既然近现代反传统思潮否定了儒家思想,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用什么来建构新时代的社会文化?在这方面,清末民初兴起了两股思潮,填补了儒家退场之后所空出的位置,一是佛教的复兴,康有为、章太炎、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梁漱溟、马一浮、熊十力等这些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有重大影响力的人物皆受佛教思想深刻的影响;二是现代西方文化的东传。这两股思潮交织在一起,对儒家的现代诠释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儒家伦理批判是其中一种表现,另一种是对儒家的哲学诠释。西方哲学传至东方,与佛教复兴思潮遭遇,形成了现代中国哲学独特的宇宙论、本体论等形而上学理论,运用这些理论将儒家思想哲学论,从而形成了熊十力、冯友兰、汤用彤、任继愈、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等现代哲学家的儒学理论,也影响了范文澜、萧公权、侯外庐、翦伯赞等现代史家的思想史诠释。儒家的伦理、政治及社会文化意义被否定之后,其思想以现代中国哲学的方式进行了创造性的诠释与转换,成为现代中国哲学的重要内容。然而,我们需要反思的是,既然儒家的伦理、政治、社会文化意义被否定了,而以现代中国哲学的面目重现于世,其意义是什么呢?这样的理论框架其实给儒家留下的位置相当狭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港台新儒家的理论创造难以逾越心性论的范围。但问题在于,既然儒家传统的天道观与伦理被舍弃,哲学化的心性论如何构成社会文化?例如,在儒家传统的婚礼中,新人跪拜天地,而在现代中国哲学的诠释中,将天换成了“本体”,我们能想象新人一拜“本体”吗?如果“本体”这样的中国哲学概念无法转换为社会文化,那么这样的儒家哲学或中国哲学有什么意义呢?
至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人们在学习现代中国哲学的时候难以产生问题意识,从而难以在其学习中形成专题化的思考。现代中国哲学本身的问题意识是从西方哲学中嫁接过来的,在相当程度上,是在用中国传统的一些思想文化来表达西方哲学中的主题,这显然不如用西方哲学术语来表达来得直接。所以,我们在哲学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发现,外国哲学专业的学生可以更容易地使用西方哲学术语来思考问题,而中国哲学专业的学生更难以使用现代中国哲学学科的术语来思考问题。究其根源在于,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如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及道教与中国佛教,其理论兴趣与西方哲学迥异。就儒家而言,儒家志在究天人之际而致天下太平,与西方哲学对存在问题、认识论问题的思考极为不同。将儒家诠释为一种儒家哲学,就会使儒家失去其原有的焦点。因为对不上焦,所以儒家在现代哲学学科中呈现出来的印象就模糊不清,学生更多是被动接受,而非自主思考。
既然儒家的哲学诠释存在不足,那么应当作什么样的诠释更好?儒家思想中当然也蕴含着对哲学问题的思考,不过,用传统的术语来说,儒家思想包括天道与人道两个方面,换成现代语术,这其实就是一种文明的人类社会建构。因此,现代儒家诠释应当放在文明论的视野中进行,而不仅仅放在哲学学科中。
二、儒家与文明论
文明这个词既是对英文civilization的翻译,也是一个固有的汉语词,《尚书·舜典》曰:“浚哲文明。”孔颖达疏云:“经纬天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文言》曰:“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可见,在中国古代经籍中,文明意味着圣人的教化大行于天下,使人类社会达到了极高的道德与智慧。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继承了这样的用法,意指社会发展达到了极高的水平,或指一个人的修养达到了极高的水平。作为civilization的翻译,文明又指称一个相对独立发展起来的社会实体,包括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文化方面的全面成就。文明论包含了文明概念的这两个层次,一方面意指一个社会实体的社会构造方式及其成就的独特之处,另一方面意指这些成就所具有的价值。
其实,上述对儒家伦理的批判与哲学诠释就已经蕴含了一种文明论,正是基于其文明论观念对儒家所出的诊断。在当时很多人的理解中,西方现代文明与其他文明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取代关系,只有西方现代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其他的文明只能称之为野蛮或半开化。既然新的更高级的文明已经被创造出来,过去的一切文化或文明都只能称之为旧物,应当予以废除。1930年,中华民国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召集蔡元培、吴稚晖等人研究民法修订事宜,其核心议题有三个,是否要有姓、是否要有家庭、是否要有婚姻。他们一致认为,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氏族社会之物将会消失。1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傅斯年挂在宿舍墙上的条幅上写着“四海无家,六亲不认”2,要求以新道德取代旧道德。
如果人类社会进化到无姓、无家、无婚姻,这将是怎样的文明?与破除家庭相应的政治思潮则是破除阶级、废除私有制,追求大同。20世纪初中国涌现出无政府主义、世界主义、天下为公的政治思潮,这与儒家传统中的大同理想不无关系。康有为、章太炎、吴稚晖、刘师培、孙中山、蔡元培、熊十力等这些近现代有影响力的人物,看似有着极为不同的思想主张与政治立场,但在下面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即人类社会无论经过什么样的发展阶段,迎来的最终阶段是相似的,那就是无家庭、无国界、无族群、无阶级、无政府的大同之世。近代以来,西方科学与社会进化论、民主思想、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东来,与中国儒家传统的大同理想相结合,形成了大同说、世界主义、无政府主义及社会主义等诸多政治思想形态。如果对世界文明的进步抱有这样的期待,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政教尚有何价值可言?因此,民国时期将经学视为“国故”和古代政治统治工具的做法,究其根本,源于一种文明论的意识,即相信现代文明将有极大之进步,而以中国古代为故旧的、不合时宜的文明。3
人类社会的文明将往何处去?这个问题极为复杂,这不仅与价值判断有关,也与社会存在蕴含的客观规律有关,人们提出的价值理想并不一定能够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实现。考虑到人类社会的一些客观特性,我们就会发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物质技术与社会组织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人心结构与总体的社会结构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这就意味着,社会竞争只是从古代社会形态转向社会形态,基于人性与人心需要而有的社会制度可能会改变形式,但不会消失,除非人性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此而言,所谓现代文明与古代诸种文明也就没有本质的区别,人性不一定会随着技术的进步与制度的变迁而进化。
中国古代社会所呈现出来的制度与伦理状况,其原因并不一定是中国人的人性如此,或是因为中国文化如此,而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族群关系这样的社会条件有更深刻的关系。例如,《二十四孝》中所展现的儒家伦理以现代的眼光来看有其残酷的一面,这并不能证明儒家伦理本身是残酷的,《二十四孝》体现的是生活物质极为匮乏的条件下人所能设想的伦理生活。如果要将儒家伦理与现代伦理作比较,则应基于相近的物质生活条件的假设。在生活物资不足以养活一家人的条件下,现代伦理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吗?因此,由古及今所取得的社会进步,究其实,未必是伦理的、人性的进步,而是外在的社会生活条件进步所带来的社会道德状况的改善。而生活条件的改善对社会道德状况改善的影响是有限度的,它无疑可以避免“郭巨埋子”式的悲剧,但难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
另外,儒家在古代社会条件下所展现的伦理精神,并不仅仅为解决生存问题而发,其君子修养恰恰是要求人们摆脱物质生活条件对精神修养追求的限制。孔子要求,“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论语·学而》);“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这种追求道义更胜于物质生活享受的思想,产生于物资匮乏的时代,但其精神价值是超越时代局限的。因此,文明论的内涵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容(如物质生活条件,法律与社会制度等)是变化的,而社会结构不变,即一个社会固有其物质、精神与制度要素,这些要素的组合构成一个完备的社会体系。这些要素之间有相互关联的一面,也有相对独立的一面。我们今天研究儒家,就需要剥离儒家中的历史性要素与超历史维度。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现代社会生活改变的是社会生活的一些内容,而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人的世界观及其价值追求,在近现代的社会变革中展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例如,现代中国电影电视剧对主角的道德要求,与中国传统的儒家对君子人格的要求,有某种内在一致性。
儒家与中国历史社会的互动已成为当代儒家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干春松在《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重回王道——儒家与世界秩序》《制度儒学》《儒学的近代转型》等著作中较为深入地揭示了儒家与中国社会变迁的关系;陈壁生《经学、制度与生活——<论语>“父子相隐”章疏证》一书深入剖析了儒家伦理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价值意义与组织作用;陈明《儒家文明论稿》一书则向我们敞开了儒学研究的广阔视域。在儒家与政治方面,近现代以来,人们往往将儒家与君主专制联系在一起,将儒家作为君主专制的思想统治工具而加以批判。中国历史社会非常复杂,运用西方术语及其思维方式未必能够将中国历史社会的特点揭示出来。儒家经历了封建制、郡县制及现代共和制漫长的历史阶段,即经历了极为复杂的制度变迁,不同时代的儒者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与制度设计,难以用某一种特定的制度形式来概括儒家的政治主张。就秦汉以降的郡县制而言,君主专制是否准确地体现了这一段中国历史的政治过程?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对用君主专制来概括中国古代政治的做法提出疑问,任锋在《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一书中将中国历代政治变迁中所展现的中国政治思想概括为治体论,这比君主专制论更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历史政治中的诸要素及其运作机制。此后,任锋又用“中心统合主义”的理论深入地刻画了儒家社会一体化的整合机制。这些研究表明当代的儒学研究已经摆脱了清末民初以来对儒家贴标签式的研究方式,已经能够深入到从中国历史社会结构与变迁机制来把握儒家思想的精深领域。这对我们重新解读《论语》一书具有重要的启发。
三、孔子与圣人
圣人是理解孔子与《论语》的重要概念。这也是古今思想差异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今人读《论语》,多欲还原历史上那个有血肉、有情感的真实的人。当然,这样的一个人与作为圣人的孔子并不必然矛盾,只是侧重点不一样,更多地强调孔子也是凡人,只不过他的道德学问高于常人。譬如李零曾提出“去圣乃得真孔子”的说法。“天纵之圣”的观念在现代已相当陌生。那么,今天应如何理解圣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云:
《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4
司马迁说,古往今来的王侯与名人不知有多少,都不过是历史长河中的匆匆过客,唯孔子一人以布衣之身而名传后世。其人其德,令他心生仰慕,徘徊于孔子故里,久久不能离去。孔子何以至于斯?
司马迁的概括是“六艺折中于夫子”。六艺者,六经也。六经即《诗》《书》《礼》《易》《乐》《春秋》,是古代王官之学,是华夏文明的载体。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说法,诸子百家皆六经之“支与流裔”,也就是说诸子百家的思想皆源自六经。虽然《艺文志》所说的诸子百家是整合进天下治理体系之后的形态,但也可以说明经学在中国传统中的核心地位。《庄子·天下》也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百家之学所称而道之者不过是六经之一端,而非六经之全体。诸子百家的出现,恰恰是六经离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庄子·天下》)的结果。所以,诸子百家并不足以代表中国文化——华夏文明,诸子百家恰恰源自华夏文明这个母体。在古人的理解中,只有六经才能够作为华夏文明的载体与象征。而孔子,是参与创制、传承六经的“集大成者”(《孟子·万章下》),是六经之义理的折中者,所以,孔子作为圣人,就意味着一种文明的象征。宋人称“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5,此之谓也。
在孔子之前,有尧、舜、禹、商汤、文、武这样的圣王,但除了孔子,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更能代表华夏文明。晚清廖季平在区分今古文经学时提出,汉代古文经学以周公为圣人,而孔子只是先师。而其所标举的古文经师刘歆在其《移让太常博士书》中说:“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记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卒而大义乖。”6“圣帝明王”是集体名词,独孔子矫正礼乐,修序制作,而特显其名。在汉代纬书中,孔子是黑帝所感生的圣人,向人间传达天意,这是汉代人看待孔子的侧面写照。
一种文明,必须由一个圣人来代表吗?在不同的宗教与文明观念中,不一定有圣人的观念,但一定有与中国之圣人功能相类的象征者,如先知。与一神信仰不同,圣人是人可以通过不断地修养与进步而达成,正如荀子所说:“圣人也者,人之所积也。”(《荀子·儒效》)所以圣人的成就应理解为中华文明的成就。如果说圣人是人积累自己的知识、修养而达成的,并且,宋明儒学以成圣为最高目标,但自孔子后为什么中华大地上再无圣人?孔子之积,非个人之积,而是集先王先圣之大成,是文明之积,是中华文明至春秋而展现出其更丰富的可能性。孔子以其过人的天赋不懈地学习、求索,将自己所得贯注于五经的整理中,传授于门弟子。于是五经与《论语》成为中华文明最核心的经典。孔子的成就标志着中华文明的成熟。
儒家所着重论述的人情、欲望、性理、礼制与修养方法,揭示的是人类自身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其他宗教与文明中也同样存在。儒家刻画了人从一种初始状态到理想状态的转变过程及其发生机制,从而构成一种普世性。儒家首先是一种人伦养成的社会教化,是中国从原始走向文明的文化载体。正是因为社会建构与国家建构所需要的条件与儒家的功能相契合,这就决定了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社会文化形成了以儒家为主导,以诸子及佛教、道教为辅助的格局。晚近一两百年来西学东渐,中国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结构哪些部分发生了改变?哪些部分是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结构中的稳定性因素?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取决于我们对人类社会共同体建构的理解深度。
1 赵妍杰:《家庭革命:清末民初读书人的憧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2页。
2 王汎森:《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44页。
3 秦际明:《文明共识与近代经学观念兴替》,《中山大学学报》2022年第6期。
4 (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31页。
5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50页。
6 (汉)班固:《汉书》,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528页。
来源|哲珠新媒体
编辑|王志远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