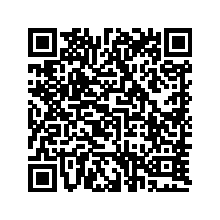学术资讯|我系龚隽教授发表文章:近代今文经学与佛学之交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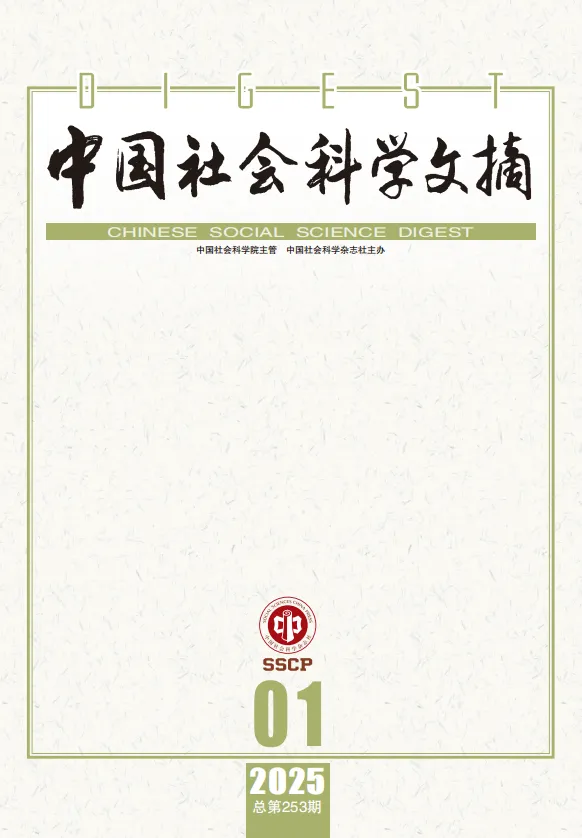
近代今文经学与佛学之交涉: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
本文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25年第1期第41-43页
文/龚隽
作者简介

龚隽,男,江西南昌人,哲学系(珠海)教授。198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图书学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87年就读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主攻中国哲学史方向,1990年毕业并获哲学硕士学位;1990年就读于武汉大学哲学系,师从肖蓵父教授,主攻中国哲学史方向,1993年毕业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93年至2001年,就职于广州华南师范大学哲学研究所,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所长。2002-2003年度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系访问学人。2002年至今就职于中山大学,曾任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教授,副所长、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佛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东方哲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科院评价研究院宗教专业委员会委员,香港中文大学人间佛教研究中心荣誉研究员(2013-2015年),佛光大学佛教研究中心通讯研究员(2014年-2015年)、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研究员(2015-2016年)、《新史学》(中华书局)学术编委,《汉语佛学评论》(上海古籍出版社)主编,《人间佛教研究》(香港中文大学)编委,《人文宗教研究》(北京大学宗教文化研究院主办)编委等。主要从事中国佛教思想史、比较宗教学及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提要
本文主要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中心,考察近代中国今文学运动中经学与佛学的复杂关系。论文把康、梁置于晚清以来今文学的思想传统中进行探究,批判性地讨论了康有为的经学、理学与佛教关系,以及他的大同世界观和天文学思想中的佛教观念。对于梁启超的佛学探讨,则主要阐析其今文学语境下的佛学论述和儒佛关系论,最后从近代经史学之转型探讨与分析梁启超佛学研究的前后变化。
关键词:今文经学、康有为、梁启超、经学、佛学
学界有关近代中国佛教思想史的探讨大都有论及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的佛学观念,而仍然有诸多未发之覆有待深究。前贤之相关研究,此文不加赘述,本文主要立足于晚清以来今文学的传统,以经史之学为主轴,深入探究这一语脉下康、梁佛学思想之源流与特点。
大致而言,清代经学在嘉、道以后,今文经学有所复兴,今文学“义愈推而愈高”,“门径大开,榛芜尽辟”,其旨趣既不像汉学家那样“说经皆主实证”,也不像宋学一般“空谈义理”,而是借经作微言大义以阐明社会政治之道。代表十八世纪今文经学的常州学派自庄存与、刘逢禄开创以来,到了龚自珍、魏源的出现,他们“兼治佛学”,在传统经学的法流中开创新局,这一点影响了晚清的今文学家。梁启超在1902年所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就提到“自龚定庵好言佛,而近令学界代表之数君子,大率与定庵有渊源,故亦皆治佛学,如南海、壮飞及钱塘夏穗卿曾佑其人也。虽由其根器深厚,或其所证过于定庵,要之定庵为其导师,吾能知之”。梁所列的几位学界代表,大都是今文学系的学人。在梁后期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中更明确了这一看法,指出“龚、魏为今文学家所推奖,故今文学家多兼治佛学”。看来晚清以来今文学者好融通佛学与经学来进行思想创造,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不过,从龚、魏到晚清今文学家的会通佛学,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变化。龚自珍特别推崇天台一系在经学方面的成绩,并希望藉此理念来整理古德经论,以与禅宗相抗。他以经学家的立场批判狂禅不习经典、“孤祖提印”等作风,并依照天台“依经贴释,理富义顺”的释经原则,试图在佛学上提振经学的地位,而主张“以佛知见为归,以经论为导”。魏源在佛教经学方面则偏重于净土经典,并以经叙方式来论究诸经之源流本末,而在思想方面,他也是倾向于会通天台教义来作阐解的。如在《观无量寿佛经叙》一文即表示要以“天台三观三谛释一切经”。可以说,嘉道时期今文经学者对佛经的论议,倾向上大都表示了与天台法流的合一。康、梁以来今文学者的佛学观念则由宗天台而转向了华严、禅与法相之学。康有为的佛学“由阳明学以入”,而“最得力于禅宗,而以华严宗为归宿焉”。到谭嗣同还是奉行“《华严》之菩萨行”,梁启超受杨文会之影响,则对于法相之学颇有推崇,他所作佛教哲学论议,如《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即以法相之理格义西方哲学,《佛教心理学浅测》也是以唯识之义印证心理科学等,而他对玄奘之推崇也远高于慧能。
一
康有为的佛学论述非常的零散,而且大都不成系统,也缺乏详密的学术论证。他在佛学方面的经历还缺乏具体的说明,从他自己所著《我史》与其弟子的记录中,我们只大致知道他在师从经学家朱次琦之后,于宋明理学有所发明,而以今文学“经世致用”的观念为主导,“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得失”。后又从陆王心学转入佛学,“潜心佛典,深有所悟”。于儒释道三教方面,康有为也“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而最终“以孔教复原为第一著手”。康在会通佛学的旨趣上重于“行菩萨行”,“以救国救民为事,以为舍此外更无佛法”,重视的是援引佛教作经世之论,所以他并没有致力于佛学在知识上的精微,而是倾向与佛教的今文经学化改造。于是,康的佛学论义就难免与他经学著述一样大都随意武断,梁启超就说“康有为本好言宗教,往往以已意进退佛说”。我们从他有关儒佛关系的论述中就可以明确感受到这一点,不过,本文尽量把康有为在他今文学脉络下融通佛教教义的方式做一些整理与阐明。
1、经学、理学与佛教。我们虽然无法详悉康有为阅读佛藏的具体内容,但有一点很清楚,即他“合经、子之奥言,探儒、佛之微旨”,倾向于以儒家经学的方式来会通佛典,并重于玄义的阐发。康有为甚至提出以儒佛会释,以佛解儒乃学问第一要门,“用佛氏说儒书,朱子有之,此是学者入门第一功夫”。摄儒入佛可以说是清代今文学会通佛学的一个传统,龚自珍就曾以天台教观去融合儒家心性之学。为此,他提出天台性具之义即是“儒家言性者十数宗”的说法。但是康有为会通儒释,更以禅和华严两系来开展,他的佛学今文学化的色彩更为鲜明。如他直接以公羊三世说来讲儒佛通义,“孔子有三统、三世,儒与佛同”。又以佛教古史传说来比附今文学之“托古改制”,他说“以佛之聪明尚托于七佛,安有七佛之事哉?孔子之托古,亦此意耳”。
具体而论,康有为还分别注疏了《论语》、《中庸》与《孟子》,其中多以禅佛学来进行诠解。如他在解释《中庸》中“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一段义理时,就以禅宗解释说“禅者马祖谓不昧因果,南泉谓作南山下水羧牛,亦同此理也”。他早年的《万木草堂口说》还分别以禅宗神秀的“时时勤拂拭”与慧能的“本来无一物”来阐释《中庸》的“不闻不睹”和“戒慎恐惧”之义。对于孟子的思想,他也是这样禅解的。他指出“孟子用六祖之法,直指本心,即心是佛也”。在解释孟子之“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一义时,说这就是“禅者养其灵魂”的“秘为自得”。 又以佛教“八风不动,入三摩地”去解释孟子“四十不动心”之义。在《论语注》(1902年)中,他还以禅宗之南北分宗来比配孔门之后学分流,指出“盖孔门之后,儒虽分八,而本始实分二宗。譬之禅家,有子广大如慧能,曾子谨严若神秀也”。康有为还从他今文学的角度指斥曾子歧出孔门大道“别为一宗”,如同佛学之小乘教,“只传小乘,而大乘犹隐”。他认为《论语》为曾子一系所辑撰,因而未解孔门之“微言大义”,“不得其精尽,而遗其千万”。
另外,康有为曾出入宋明理学,故其论理学处也大都会通佛教来做论断。他认为“宋儒言理深,然深之至,则入于佛”,“宋士大夫晚节皆依佛,宋儒皆从佛、老来”。他同样有以禅来释义理学的,如说“宋儒之学,皆本禅学,即孟子心学”。在论陆王心学时,他一面说陆九渊“直接本心,得于佛学”,又说阳明学的功夫论“征以《易》之终日朝乾夕惕”,而实际“已入佛学”。
在儒佛互释方面,康有为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比较模式,他发现儒佛虽然在思想上可以贯通,却不能说都是那种思想上的同类相应,而有时候正表现在其相反相成的方面。他主张要注意到“佛与孔子相反”的一面,认为这是孔佛进行比较的一个前提,所谓“佛与孔子极相反,然后能立”,因而“凡言孔子之道,必以外教比较方见”,即会通孔佛还必须从其思想的差别对峙处去观其会通。如他就这样比较孔佛之异:“孔子之义在立差等,全从差等出。佛法平等,即无义也”。在《康子内外篇》(1886年)中,康有为还以阴阳相反相成之理详尽地解说这类儒佛相济之道,“圣人之教,顺人之情,阳教也;佛氏之教,逆人之情,阴教也。故曰:理惟有阴阳而已”。“孔子之伦学民俗,天理自然者也,其始作也;佛教之去伦绝欲,人学之极致者也,其卒也。孔教多于天,佛教多于人;孔教率其始,佛教率其终;孔教出于顺,佛教出于逆;孔教极积累,佛教极顿至;孔教极自然,佛教极光大。无孔教之开物成务于始,则佛教无所成名也”。最后他结论说“是二教者终始相乘,有无相生,东西上下,迭相为经也”。于是,在儒佛比较的方法上,康有为是会其同异而为之说。最明显的例子是他会通佛教与易学,一面认为“佛与《易》近”,如佛教所说“以无为有,空诸所无”,即相当于易学中“《屯》、《否》之象,发《剥》、《革》 之义,陈亢极之悔,终《未济》之卦也”;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必须看到“其所异者”,如“佛说无生,故欢喜而游戏;《易》入人伦,故恐惧以寡过耳”。
康有为论儒佛关系,大都没有展开辨析,而多出于一时随兴感悟,其中虽不乏偶有洞见,多数皆为牵强附会和“曲圆其说”。他的儒佛思想比附中具有公羊学家那种“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最明显的例子如说“达摩如儒之刘歆,六祖如郑康成”,这种附会几乎完全不需要理由与解释。又如他以今文经学家所惯用的天人感应说来阐发中印地理之别而导致儒佛的不同开展。他认为圣贤也无法跳出天文地理的影响,所谓“非圣人能为之也,天也”。他根据这种地理环境决定论指出,孔子“未尝远行”传儒教于海外,是由于孔子居所“以环境皆山,气无自出”,所以“孔子之教,不能出中国”。而佛教与基督教之传弘四海,“投身传教于异域者,盖地势使然”。又说日本“为天山、金山之余气”,气薄而往复,所以无法生产圣人(“不能复生圣人”),而印度“为昆岑中龙”,其地气能够出产“以平等为教”,并“造为文学、政教”的佛陀。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康有为公羊学说儒佛,并不遵循知识的轨则,而本质上是一种“义理的发明”。康有为儒佛关系论中的可怪之论可以说是他的今文学修辞策略的一种自然的开展。
2、从大同之境到天学之论。有学人试图阐明作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儒家未来”图景,康有为大同思想中暗藏了对于西方近代价值的诉求。大同说的成书与思想都有其复杂性,这里主要讨论大同之境与佛教教义的关系。康有为的融通儒佛,禅学以外便是华严了,他说“《华严经》与《四书》、六经比较,无不相同”,因而提出“孔教者,佛法之华严宗也”。梁启超也肯定了康有为的思想是“以华严为归”的,而“华严奥义,在于法界究竟圆满极乐”,此即是大同的境界。梁启超还就大同说的“原理”进行了分析,指出“大同根据之原理”,就在“众生本一性海,人类皆为同胞”,此即是华严无碍之界。于是就有学人就提出康有为大同世界的设计“完全脱胎于佛教十法界观”,此论未免过于渲染《大同书》的华严论色彩。
实际上,《大同书》仍然是康在今文学的基调上融摄了佛教思想,并以己意进退而成。如《大同书》对今文三统三世之“乱世”解说,就援用到佛教四谛论的思想而在首部即论“入世界观众苦”一义:“故据乱之世,举世间人皆烦恼人也,皆可悲可悯人也”。同时他还仿照佛教论苦之分类,把乱世众生之苦析分为六类38种。特别有意思的是,《大同书》中还以今文学三统三世的历史观来阐释儒家与佛教戒杀素食理念与策略之间的差异。康有为认为孔子“立三统三世之法,据乱之后,以升平、太平,小康之后,进以大同”,而儒家也正是以这种渐进主义的方式来逐步转向戒杀仁慈。在他看来,儒家到极致也主张戒杀,只是从乱世到太平世之间有一个过度期,佛教之戒杀是等到太平世才完成的景象。他说“孔子之道有三:先曰亲亲,次曰仁民,终曰爱物。其仁虽不若佛,而道在可行,必有次第。乱世亲亲,升平仁民,太平爱物,此自然之次序,无由踵等也。终于爱物,则与佛同矣。然其道不可易矣,大同之世,至仁之世也,可以戒杀矣”。于是,他颇有想象力地提出三世不同的戒杀程度:“故戒杀者,先戒杀牛、马、犬,以其灵而有用也;次戒杀鸡、豕、鹅、鸭,以其无用也;终戒及鱼,以其知少也。是故食肉杀生,大同之据乱世也;电机杀兽,大同之升平世也;禁杀绝肉,大同之太平世也,进化之渐也”。在康的融通儒佛中,这类可怪之论还相当之多,我们这里就不加细究了。
康有为有关大同思想的论述矛盾重重,这里只就其大同之境略加阐明。他一面提倡大同世界的超越至上性,指出大同之乐土胜于一切宗教圣哲之境,甚至泯灭了包括佛教在内的一切宗教。所谓“大同之世,太平之道,人人无苦患,不劳神圣仙佛之普度,亦人人皆仙佛神圣,不必复有神圣仙佛”。但有时他又提出佛教境界“尤出乎大同之外”,成为比大同更为理想的世界。这时他并没有以华严法界来讲大同的理想之世,而把大同极境归宗于禅,以禅宗之绝言名相为大同世界的最后极境:“故大同之世,惟神仙与佛学二者大行。盖大同者,世间法之极,而仙学者长生不死,尤世间法之极也。佛学者不生不灭,不离乎世而出乎世间,尤出乎大同之外也。至是则去乎人境而入乎仙佛之境,于是仙佛之学方始矣。仙学太粗,其微言奥理无多,令人醉心者有限。若佛学之博大精微,至于言语道断,心行路绝,虽有圣哲无所措手,其所包容尤为深远。……故大同之后,始为仙学、后为佛学;下智为仙学,上智为佛学”。这些论述上的矛盾性都表示康有为在“日日以救世为心,刻刻以救世为事”的情形下所开展的大同理想建构,根本是在学术上还没有来得及充分准备就急于上阵的,因而他的大同世界经常是简单化地以理想之境为故实了。
康有为在畅游其仙佛之境后,则进入了“天游之学”,这具体体现在他晚年著述的《诸天讲》(1926年)一书中。有趣的是,在《大同书》中,佛教成为康有为乌托邦理想中的极境,而进入天学研究中的康有为突然来了一个思想上的转折,这时候他从大同世界的仙佛玄境回向人间,不再以宗教而是更倾向于以近代科学的天文学知识为权衡,去融通乃至于批判经学与佛教宇宙观。康的这一思想转型,也多少缘于清代的思想语境。
中国古代经学即包含了天文学(天学)于其中,天学本身就是经学内部的一个传统。“天算者,经史中所固有也,故能以附庸之资格连带发达,而他无闻焉”。而今文学家尤好天人感通之论,并对天学有所关注。清代的天算学有所拓展而以梅文鼎为代表,“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梅氏之学既不简单地“株守旧闻”,而是以“西人为异学”,融合中西而又“无主奴之见”,梅氏把近代西方的天文算学知识容纳到经学之中,这对传统中国天算之学有一定的冲击。晚清以来,西方天文学仍然影响深远,蒋方震在为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写的序中就说基督教所带来的西方科学知识到康熙以后,“截然中辍,仅余天算,以维残垒”。梁启超也发现,清代考据学的科学精神并没有运用于自然科学的开展,不过原本就附丽在中国经学中的天算学“自王寅旭、梅定九大启其绪”以来,在清代经学中却发扬光大起来,可以说天学在各类实用科学中一枝“独盛”。
康有为晚年的经学颇涉及天学,而又深受近代西方科学运动之影响。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天文地学等都包含了社会政治内容于其中,因而不能仅从科学史的角度,而必须参考政治史的视域来理解中国的天学,这当然是深刻的洞见。如清代今文学家龚、魏治边疆地理学就好“附以论议”,这一风气使得其后“治今文学者,喜以经术作政论”。不过需要注意的是,清代经学中的经验主义也蕴含着融合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可能性,清代的经学,包括今文学的法流中也暗藏了这一伏流。清代今文经学的兴起并非一味复古旧学,龚自珍就主张“不必泥乎经史”,而要“通乎当世之务”,表现在天文学方面,就是他“摧烧汉朝天士之谬说”,批判了西汉经学中五行灾异之说,而主张以新近的天文学知识去剖析天象。康有为天学的论述中似乎一定程度地跳出了传统经学的巢穴,而倾向于以他所理解的科学的天文学知识来辅翼或者扶正固有经学或佛学中的知识局限甚至错误。康有为一方面“探儒、佛之微旨”,而同时也参究“中、西之新理,穷天、地之赜变”,在他今文经学的发明中究天人之际,而融通儒、佛及西方近代知识,试图对传统天学的知识进行拓展。
与当时流行的用西方天文学知识来证验佛典暗合的作风不同,康有为一面延续中国传统的天学思想,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经学天算学的藩篱,而以西方的科学观对包括佛教在内的传统天学知识进行了质疑与批判。康有为从光绪五年游历香港和八年道经上海时,都对西学有所接触与研读,之后还曾购买《万国公报》,对于其中之西方科学知识皆有“新识深思”。在天学的方面他并没有醉心于大同世界中的玄学佛境,而是把他所理解的近代“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框架和“自然法”,重新勾画对自然的图景与原理。在他看来,甚至任何历史与宗教的学说在作为科学知识的天文学方面都必须服从于他所谓的近代知识才能获得其自己的合法性。于是他把传统今文学中有关自然宇宙的知识从“历史的叙述”发展为一种“科学的叙述”,在《佛之神通大智然不知日月诸星诸天所言诸天皆虚想篇第十二》中,康有为以近代天文学的知识批判了佛教经典中各类天说的观念。他援引《起世经》、《婆沙论》、《顺正理论》等佛教经论中有关须弥山诸天的说法及日、月、寒暑、盈亏之说,又引《大集经》中佛说二十八星宿之说等,康有为认为,佛教在天学方面的知识因为受限于观察工具,因而从近代西方天文学的观察与推算来看,佛教有关天文学的说法大都是错误的。他甚至说佛陀虽“能穷极诸天”,也只不过“穷及日界”而已,对于银河关内的恒星,“佛已不知不识”,更况银河天以外的天际。他甚至批判《起世经》中有关天学的说法“其不知妄言,犹谬甚矣”。康还否认佛教所说“须弥上塔柱诸天”的存在,指出这些与近代天文学的观察有冲突,他指出如果运用天文观察仪器“人人握镜能见,绝无此物”。他同时还表示佛教天文学说在理论上也与近代天文学的知识相抵触,因而不值得信任:“惟此绝长塔柱假有之,与月行绕地之轨道相碍相触,或与金、水、火、木、土诸星轨道相触,则必不能有耳”。可以肯定,康有为的天学论确实一定程度地表现了清代经学中那类经验主义的倾向。晚年的康有为似乎更相信近代经验科学知识的普遍有效性,他认为作为宗教的“各教主生在古昔,未有精镜,谈天无有不误”,因而本于宗教性的推度所得出的宇宙知识与科学的观察“相去太远,误谬亦已大甚”,只能当作“随意报议推算,非谓实也”。
虽然康有为的天学知识不能如他自己所说“大讲西学”、“尽释故见”,但康有为时期的公羊学正逢中国已经进入了欧洲中心的“全球知识”成为支配性知识的时期,因此儒家经学必须包容这一“全球知识”的框架才有可能成为大同世界的万世之法。有学者发现康有为晚年的经学思想中具有一种“科学主义的普遍主义”,在他的天学观中,我们特别可以感受到他晚年经学注重的是如何努力使儒佛之学成为“有关世界的普遍真理”。 这时候,他更愿意把传统今文学的经世致用接轨于西学,从社会政治转向到自然世界。因此与其说康有为将天学政治化或宗教化,毋宁说是近代化与科学化。
二
梁启超早年受学于康有为,接受了包含佛学在内的公羊学教育,康有为当时在草堂教育即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借公羊“三世说”宣传维新变法。受今文学的影响,梁启超早年对于佛教就颇有好感与推崇,除了在广州万木草堂受康的佛学影响外,梁在维新变法时期还与友人谭嗣同、夏曾佑、汪康年、孙宝瑄等常切磋佛学,他曾表示自己虽然“不能深造,顾亦好焉,其所著论,往往推挹佛教”,实际上梁启超早年对于佛学之嗜好有时到了“务道痴心”的程度。
1、今文学意识下的佛学应用。梁启超早年今文学立场与康有为如出一辙,他曾直率地表示自己早年是今文学“猛烈的宣传运动者”,还称许“南海说经之微意”即在发挥《公羊》三统三世之学义,以“解二千年来人心之缚,使之敢于怀疑,而导之以入思想自由之途径而已”。他在为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所写“叙”文(1897)中就以公羊三世之说讲孔子之学,又以佛教华严无碍之境解读公羊学之大同极境。
梁启超主要从儒佛不二,而皆倾向于济世成物的意趣上来讲孔佛一贯之道。他特别推崇今文学治经以致用的传统,认为“凡学焉而不足为经世之用者,皆谓之俗学可也”。梁启超讲孔佛不二,主要是根据佛教大小二乘之判来会通儒门宗旨。他认为大乘佛教讲求济世而非舍世的菩萨行,正可以会通到儒家,特别是今文学所解说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上来理解。他指出儒家之经教也可析分为“普通之教”与“特别之教”,这就如同佛教之分小、大二乘。其中《诗》、《书》,《礼》、《乐》等经为“普通之教”,而“凡门弟子皆学之”,此即相当于佛教之小乘;而《易》与《春秋》这类今文学所特别倚重的经典则为“特别之教”,“非高才不能受焉”,这就类同于佛教之大乘。他还结合公羊学之三统说来加以格义,说“普通之教”即是相当于“小康”之义,而“特别之教”才是“大同”之境。他还为公羊学的大同之教理致高深,不为时解作了这样一段佛教化的辩护:“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说法有权实之分,故立义作往相反。耽乐小乘者,闻大乘之义而却走,且往往执其偏见以相攻难,疑大乘之非佛说。故佛说《华严经》时,五百声闻,无一闻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闻”。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1898年)》“谭嗣同传”中也同样是以佛教大小二乘的分判模式来会通今文经与佛教,他认为孔子治《春秋》即是“大同小康之制,千条万绪,皆为世界也,为众生也”,在梁启超看来,这即是大乘佛教“悲智双修”的精神。他还结合公羊学的三统三世说,并以佛教之法相学,而不是康有为所惯用的禅与华严来进行格义。更有意味的是,在梁的佛教格义中,公羊学的乱世、小康、太平三世之说已经被佛教化的过去、现在、未来等所替代,梁启超以他解释原则中的“法异而不异”来打圆场。他这样说“《春秋》三世之义,救过去之众生与救现在之众生,救现在之众生与救将来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此土之众生与救彼上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救全世界之众生与救一国之众生,救一人之众生,其法异而不异,此相宗之唯识也”。如果可以这样不顾解释章法或解经家法自由地会通儒佛,那真成为梁自己所说已到了“通乎此者,则游行自在”的地步了。可以说,梁启超早年以今文学所作孔佛不二论,多少有了今文家那种好做比附以通经的倾向。
梁启超论佛教与群治关系也可以看成为今文学经世致用模式下的佛学论述。群治乃近代今文学所论述的一大社会政治议题,梁启超对于国民性(如新民说)的思考,引发他对宗教信仰在社会政治中作用的反思。他的问题是“中国群治”是否需要宗教性的信仰作为依托。他认为从世界文明的角度言,一个社会群治的问题是需要宗教信仰作为基础的。“中国群治当以无信仰而获进乎? 抑当以有信仰而获进乎,是也。信仰必根于宗教,宗教非文明之极则也。虽然,今日之世界,其去完全文明尚下数十级,于是乎宗教遂为天地间不可少之一物”。在这里,梁启超所关心的宗教并非就超越解脱的意味来说,而是现代社会中宗教的效应。“今日之世界”的此在性关联的正是他对国家、国民“近代性”问题的思考。梁正是在经世致用理路下来规划他的 “应用佛教”,所谓“此佛学所以切于人事,征于实用也”。
在梁启超看来儒家只是“教育之教也,非宗教之教”,所以无法起到宗教之特有功能,而作为洋教的基督教“与我民族之感情树凿已久,与因势利导之义相反背也”,也无法适应于中土,因此他认为只有佛教才能够担此大任。关于佛教适于民性之改造,梁提出来六点意见,我们仅选择与今文学解释有关的几条略作阐明:一、“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他认为佛教讲究的信仰是知信,即“于不可知之中,而终必求其可知者也”,如此则可以完成儒家理想中的知识与信仰之调和。二、“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独善”,这类大乘佛教的精神可以完成“舍己救人之大业”,此亦是今文学救世之旨趣。三、“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厌世”,他认为佛教的这一观念可以融贯到经学的大同理想,从“小之可以救一国”,到“大之可以度世界”,由人间而进化到大同世界的境界。关于第四、第五之内容,即佛教信仰乃“无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别”,梁启超还是以公羊三世之说来加以会通,指出其他宗教只适用于乱世与小康世界,唯有佛教贯通三世上下,他说“他教虽善,终不免为据乱世小康供之教;若佛教则兼三世而通之者也”。梁的这一佛化三世说实际上已经歧出于康有为的公羊学说,康的大同论主张儒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乱世与小康阶段,而进入大同世界后,则为仙、佛玄境,而尤以佛教为至上。
清代今文学家论经世特别受佛教影响而注重于人的精神力量,龚自珍就以佛教的“心力”说作为社会改革之动力。他在《壬癸之际胎观第四》中说“心无力者,谓之庸人。报大仇、医大病、解大难、谋大事、学大道,皆以心之力”。梁启超穷尽精力探求社会改革之道,他发现社会革命通常都是始于少数“仁人君子”的觉悟与启蒙,但少数人如何可能影响和扭转“举国人相率以造”的恶业,“熏恶根以向净”,达到“以易天下”的革命成功?在《雪浪和尚语录二则》一文中,梁就以佛教熏习义来阐明社会变革中心力之重要。他认为唯有“心力”可以转此乾坤,“自古虽极泯梦之世,未尝无一二仁人君子,自拨流俗,而以其所学风天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吾侪之所以不尽为禽兽,皆赖此一二仁人君子心力之赐也”。可以说,梁启超早期的儒佛教关系论述,几乎都是依附在清代今文学传统的脉络下来开展的。
2、从今文学到史学。今文学的治经除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引申,同时也把解经与历史学的考述结合起来。梁启超就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只是在康有为那里,历史的考证服务于经世的阐释,因而经常掩没了历史学知识的开展。康有为在经史学关系上仍然是经学家的立场,所以他认为“史学大半在证经,亦经学也”,即把史学看做是经学的附庸。梁氏最初提倡的新史学也还没有完全脱离今文学的窠臼,他提倡“新史学”是因为他当时认为经学已经不足以经世,“而史学可以经世”,所以他一面批判旧式的史学“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同时又把新史学的原则确认为“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
梁启超曾经自嘲自己“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这对他学问的转型来说也是恰当不过的描述。他特别重视史学传统,虽然他于1902年首次推出《新史学》,但那时候梁的新史学观念主要还在政治而非学术。1920年代以前梁启超的佛学著述也主要是以今文学家的方式“借事明义”,注重的是“圣经微旨”,所以他援引佛教也是以阐明经世之意为宗旨。他对于经教的解读方面虽然不像康有为那样好做可怪之论,而今文学的作风也使得他的佛学阐释“所托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
进入民国,特别是1920年代之后,新史学的观念逐渐转向了学术史本身,而客观主义的知识理想渐成为新史学之目的。这时候梁的史学观念受到“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这一运动就主张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整理国故学。胡适1923年在他著名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就表示“整理国故,必须以汉还汉,以魏晋还魏晋,以唐还唐,以宋还宋,以明还明,以清还清”,这种“各还他一个本来面目”的学术精神倾向于以历史专业化的方式去还原历史真相。胡适同时强调了宗教史作为专门史的意义,而在研究的视域方面,主张“虚心采用”西洋学中“科学的方法”,以及他们在材料方面“无数的成绩”。这些学术观念在梁启超1920年代后的佛学著述中都可以找到鲜明的印证。
实际上,从梁启超早期流亡日本一直到20年代后所作佛学史论著,都广泛参考了日本及欧美近代学术研究的成果。如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1902年)论及中国佛教史部分,他就承认其论述不少是采自日本近代佛学研究。到梁晚年著《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1926-1927年)论佛教史的研究时就更趋于“科学化”,这时候他主张“用科学精神,诚实的研究佛教”。他不仅关注日本研究,还注意到西方佛学研究的成果。如在讨论玄奘传的问题时,特别提到关于那烂陀寺的研究“西洋文字日本文字比较中国文字多得多”,而他《佛教与西域》一文亦广泛采用欧洲学者的成果。
在20年代写作《清代学术概论》时,梁还专门反思了自己与康有为的今文学运动,说自己经常不满足于康有为经学论述中“实极大胆之论”。他批评康的经学由于“好博好异”而“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他对自己前期学术过于讲经世而影响学术规矩也颇有悔悟之义,表示自己“抱启蒙期致用的观念,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颇失为经学而治经学之本意,故其业不昌”。1922年他写作《中国历史研究法》,这时他对历史学的看法已经与1902年提倡新史学大为不同,不仅主张历史学的书写应该做“纯客观的研究”,“欲为纯客观的史”,而且还特别对他前期所尊奉的今文学家法中托古改制和微言大义的学风进行批判,说《春秋》学中“寓褒贬,别善恶”及“微言大义,拨乱反正”的历史观“乖莫甚焉”。 梁指出今文学这种好“搪古书片词单语以傅会今义”的方式会滋生学术研究的多种流弊。
虽然梁启超认为佛教是具有科学倾向的“哲学的宗教”。如他在论究印度原始佛教的“哲学”时这样说“佛教哲学的出发点,非玄学的而科学的”,“对于一切现象,用极忠实的客观考察法以求得其真相,不容以自己所愿望所憎嫌者而加灭于其间”。在中国近代思想语境下,他把佛教比配为哲学,特别是具有科学性质的哲学,这本身就是对佛教合理性的一种叙事策略,无疑是要为佛教在近代思想系谱中挣得一席之地。
学术史观念的演变直接影响到梁启超的佛学研究,虽然梁启超高推佛教哲学的价值,而在他的佛学著述中只有少数论文涉及到佛教教义或哲学的论述,如《近世第一大哲康德之学说》(1903年)以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格义康德哲学,他说“以康德比诸东方古哲,则其言空理也似释迦,言实行也似孔子,以空理贯诸实行以似王阳明”。他还以唯识哲学来进行解义,指出“康氏哲学大近佛学,此论即与佛教唯识之义相印证者也。佛氏穷一切理,必先以本识为根抵,即是此意”。
梁于20年代的佛学撰述是以史学为主的,这时他努力于化经为史,试图摆脱他过去在今文学阴影下的佛学论述方式。而从佛教史的撰述来看,20年代后他的佛教史观也发生来一些变化。在他前期有关学术思想史的写作中,大凡涉及到佛教史的部分基本是在中国思想史的架构内来加以论述的。1920年代为了完成计划中的《中国佛学史》,他突破了早年只从中国思想传统来论述佛教史的方式,而希望把中国佛学史放置于从印度到中国的发展脉络下来加以观察。梁启超的这种中国佛教史书写中的印度学观念,与当时中国史学界所流行的古史学运动有着深刻的关联。
民国初年,中国近代历史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治学之士,竞言古史”的局面,近代中国知识史的研究中这种古史运动特别重视溯源性的探求,他们假定对起源的回归意味着“回到人类存在可靠和原本的意义”。古史研究兴起与溯源性思考成为当时中国历史学研究的一大潮流。顾颉刚1940年代所发表的《当代中国史学》中就指出,古史研究成为近20年来史学研究的中心议题。他发现这是由西方新史学的观念与清代经学“疑古”思潮的结合,而引发了“史学上寻源心理的发达”。疑古而溯源到古史中去求真,正是近代中国知识史书写背后的一个基本观念,这一观念也引起了学者对于“古代宗教和神话的研究”。
梁启超所师承的今文学本来就有“疑经”而探古的传统,他把这种溯源古史的家法用于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如他作《佛教之初输入》(1920年)一文,其中就对汉明帝求法、《四十二章经》与《牟子理惑论》等中国佛教初传时的历史与文献进行详密考订。古史研究的风潮使得梁启超注意到,对中国佛教的理解其实是需要往前推进一步,有必要从印度到中国的历史流变中去求寻解答,他说“我们要认真知道佛教全部变迁的真相,非从小乘研究大乘的来源不可”。他于1922年所写《大乘起信论考证序》时就有这样的认识,指出“吾以为今后而欲昌明佛法,考其第一步当自历史的研究始。印度有印度之佛学,中国有中国之佛学。其所宗向虽--,其所趣发各殊,调宜分别部居,溯源竞流”。所以他特别注重从历史次第的演化来看佛教是如何中国化的。有关中印佛教史的关系,他有这样的说法:“凡一教理或一学说,从一民族移植于他民族,其实质势不能不有所蜕化,南北橘积,理固然也。佛教入中国后,为进化,为退化,此属别何题,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浸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掺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数百年而始成熟,其进行次第,可略言也”。于是他治中国佛教史,自然会考镜源流地转进到印度佛教,甚至印度原始、部派佛教那里去开展,他的《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原题印度之佛教)》(1925年),《读《异部宗轮论》述记》(1920年)、《说四阿含》(1920年)等,都是这一古史探源观念下的产物。另外,梁还受到20年代历史学研究中史地学之影响,他对印中佛教史的研究亦不限于教理史,而是延展到佛教地理与佛教为主的中印交流史等议题,为此他撰作了《佛教与西域》、《中国印度之交通》等,这大抵与2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界有关边疆地理学研究的兴起有一定关联。
近代历史学有一些关键性的观念,如历史发展的“进化论”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西方的这种史学观念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也直接或间接通过日本而影响到中国思想学术界,一时成为史学论述之典范。而传统佛教史观念却相反,其坚信法的历史是经由正法到像法,最后到末法流转衰变的过程。进化论模式作为民国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大流行观念,对传统佛教史观带来相当大的冲击。梁启超的新史学相当程度地接受了西方近代史观的洗礼,但还是有所保留,这特别表现在他的学术史观上。晚年梁启超的学术史书写一方面逐渐跳出了他早年经学中那种公羊三世说的历史图式,而他代替这一史观的思想资源,并非当时盛极一时的历史进化论,而恰恰是取自佛教有关法流变灭的历史观念。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就明确表示“佛说一切流转相,例分四期,曰生、住、异、灭。思潮之流转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启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蜕分期(异),四、衰落期(灭)。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其发展变迁,多循斯轨”。 他有关中国佛教史的纲要性论文《中国佛法兴衰沿革说略》中也大抵是以这样的历史图式来建构,而把两晋南北朝佛教作为“输入期”(相当于“生”),隋唐佛教为“建设期”(相当于“住”),到唐末转衰(相当于“异”),“唐以后殆无佛教”(相当于“灭”)。可以想见,当梁启超试图以近代启蒙主义的史学观寻源探流地重新书写包括佛教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学术史的时候,他仍然折回到传统佛教史观中去寻求思想历史的进程建构,他的学术史研究就这样在有意无意间进退于近代与传统之间。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编辑|黄万豪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