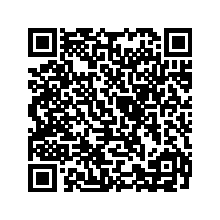学术资讯|我系蔡祥元教授发表文章:技术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未来哲学的两个版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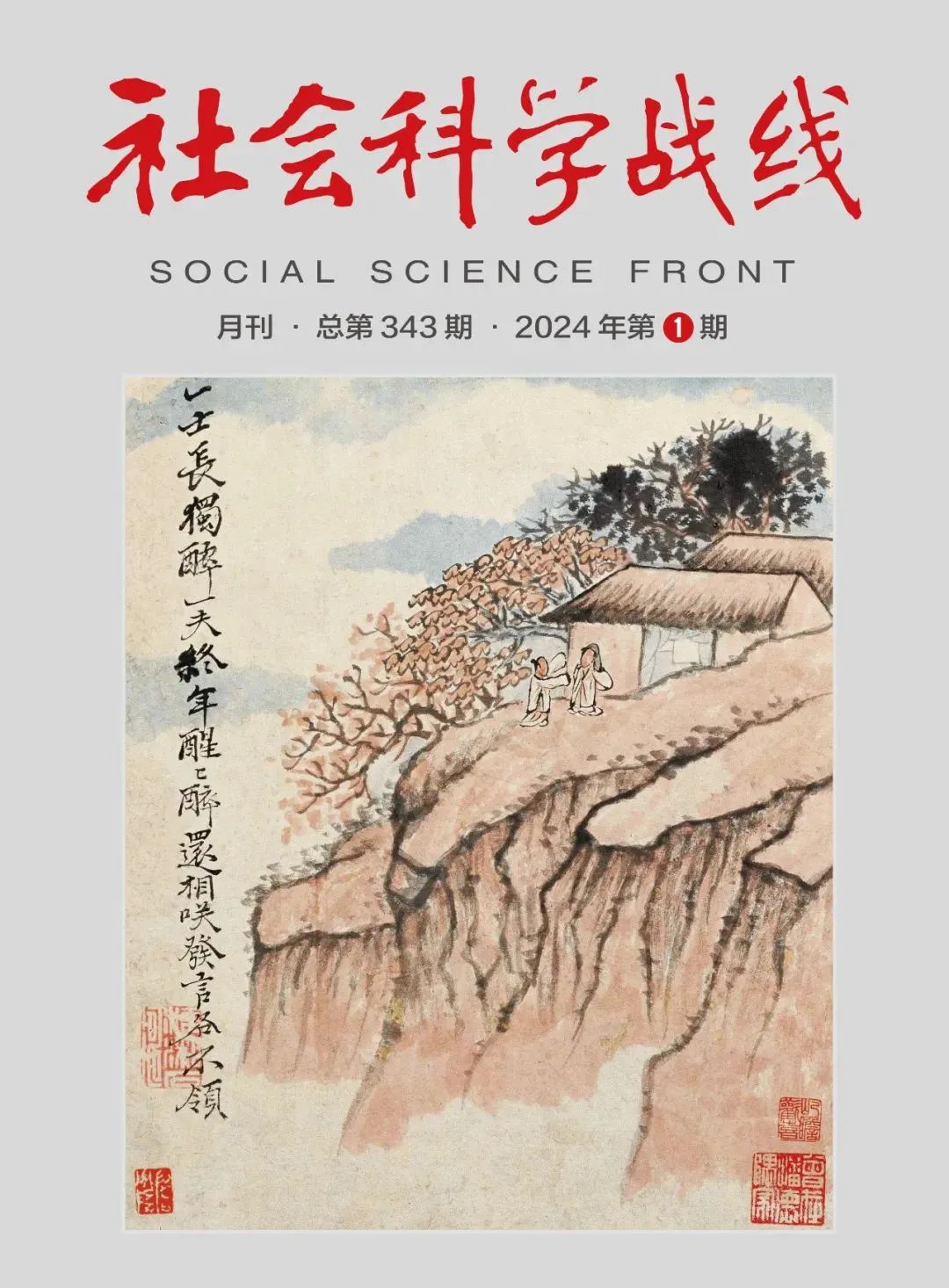
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

蔡祥元,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
技术主义还是人文主义——未来哲学的两个版本
未来哲学,简单地说,就是面向未来的哲学。
国内首倡未来哲学的学者是孙周兴教授,他立足尼采哲学,借鉴海德格尔的技术批判,参照西方地质学家有关“人类世”的概念,建构了有关哲学之未来的思想。
结合孙周兴这里的相关论述可以看到,他主张的未来哲学有以下两个基本特点:
孙周兴的未来哲学思想是在尼采未来哲学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因此,与孙周兴的解读不同,笔者以为尼采虽然批判传统哲学与宗教,但他并不反对人的自然性,相反,他渴望回归和重溯的“大地”正是我们世间的自然。
在《善恶的彼岸》中,尼采从正反两个方面来刻画他心目中的未来哲学。
为了更好地看清人文主义未来哲学与经典人文主义以及与技术主义未来哲学的区别,我们这里以技术为尺度对它们的特征做一个简要概括。
本文原载于《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1期
来源|社会科学战线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