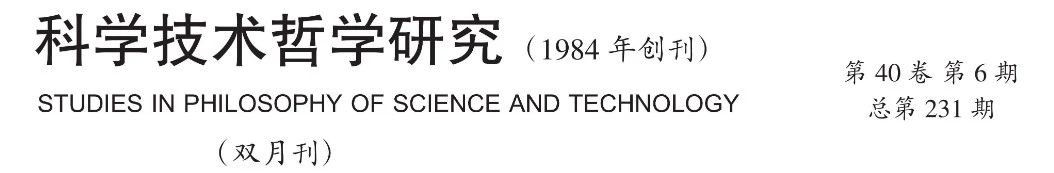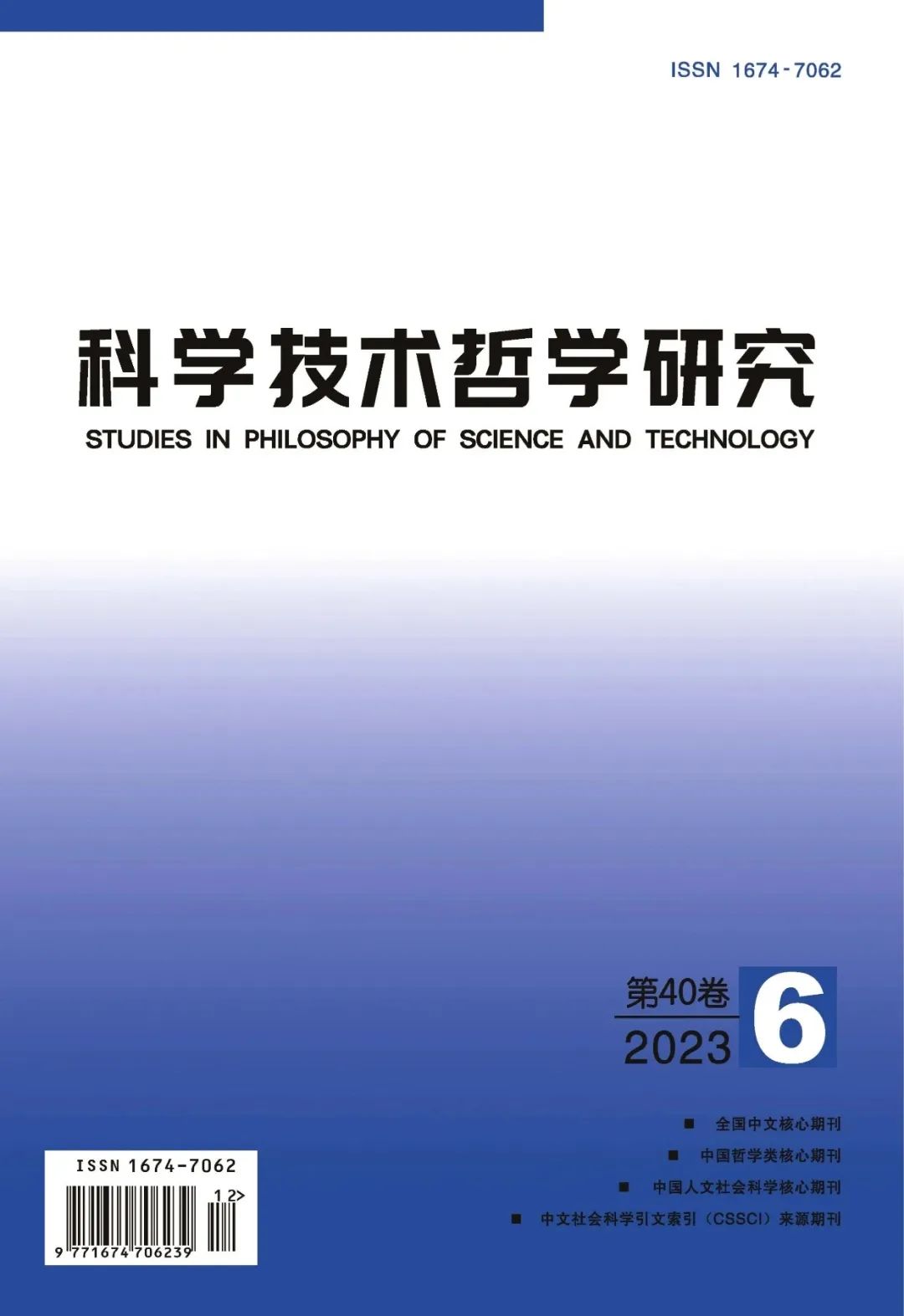在元伦理学领域,道德实在论的本体论困难推动了道德非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 错论作为一种非实在论路径,主张生活中关于道德指称的客观事实和属性完全不存在,所以根本不需要做出本体论承诺。 这一立场最初是由麦凯(John Mackie)提出的,他认为“虽然大多数人在作出道德判断时,除了别的事情以外,都暗自断定,是在指向具有客观规定性(objectively prescriptive)的某个东西,但这些断言全都是错误的。 ”[1]对此,麦凯提出了两个核心论点: 一个是怪异性论证(argument from queerness),还有一个是相对性论证(argument from relativity)。 怪异性论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是形而上学方面的论证:
(a) 如果存在着道德事实,那么它们将是完全不同于宇宙中其它事物的非常怪异的一种对象、性质或关系;
(b) 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宇宙间存在着这种怪异的事实;
(c) 因此,并不存在道德事实。
其次是认识论方面的论证:
(d) 如果存在道德事实,那么我们应当能够察觉到它们;
(e) 如果我们能够察觉到它们,一定是通过某种道德知觉或直觉的特殊官能,即一种完全不同于我们日常认知器官的怪异的官能;
(f) 并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存在这样怪异的官能;
(g) 因此,并不存在道德事实。
而另一个相对性论证主要是从道德相对性的角度来论证道德事实的存在问题,具体论证如下:
(h) 在我们生活中存在着大量根本的道德分歧;
(i) 而对此最好的解释便是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定性的道德事实;
(j) 如果任何理论是对某种经验现象的最好解释,那么它就是正确的;
(k) 因此,没有所谓的客观规定性的道德事实。 [2]
综上所述,道德错论主张: 第一,道德论说具有事实和认知意义,它是一种对外部世界的断言,具有适真性。 因此,它属于一种认知主义。 第二,所有的道德论说都是系统地错误的,它们所断言的道德事实和属性全部都不存在。 然而,无论我们是否有理由以道德上正确的方式生活,总是会有一种道德上正确的生活方式存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道德事实的必要性提供了理由。 就像如果有神论是真的,那么一种关于客观正确的生活方式的概念可能是有意义的。 但是,为什么上帝发出的命令在适当的意义上应该是客观规定性的呢? 毕竟,“使用客观道德价值概念的人将假设有一些要求只是简单地存在于事物的本质中,而不是成为任何人甚至上帝的要求。 ”[1]59所以,其实我们真正需要的并不是对道德事实和属性的本体论承诺,而是类似于上帝创造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之间的这种便利的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麦凯主张在坚持道德错论的同时,也呼吁不要放弃日常道德话语与实践。 道德错论的提出不仅给道德非实在论提供了一种发展路径,也给传统的道德实在论和认识论带来了新的挑战。 但是,仔细分析的话可以发现麦凯提到的道德价值观的古怪之处并非完全显而易见。 如果说道德理由在形而上学上是怪异的,那么似乎所有的理由在形而上学上都是怪异的,包括推进某人行动的理由,以及相信我们最好的科学所假设的实体、属性和关系的认知理由等。 所以,麦凯集中攻击的实际上是康德所提到的那种绝对命令,毕竟这种命令的要求呈现了某种奇怪的客观约束力。 如果遵守这一要求并不能达到我的目的,那么我不应该伤害别人的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这看起来像是一个奇怪的事实。 而且,这种怀疑似乎也是对基本的非目的给定理由(non-end-given reasons)的关注。 富特(Philippa Foot)也发现了这点,并将道德禁令与礼仪和俱乐部禁令进行了对比。 一个给定的礼仪规则可能会告诉我做a或不做a,它对主体的特殊的、偶然的目的并不敏感。 但很明显,个体没有一个基本的理由遵守礼仪规则,尽管它的禁令明确地针对所有人。 道德家可能会说道德与礼仪不同,但富特发现这种说法令人费解。 比起绝对命令,也许把道德当做和礼仪一样的假言命令更为合适。 [3]总的来说,对于形而上学的怪异性的论述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首先是对非目的给定的理由有一个基于概念的标准,而道德理由没有达到这个标准。 例如,人们经常认为,规范性理由必须能够激励个人,或解释他们的行动,或说服他们采取行动。 但道德理由有时与一个人的欲望相反的,因而无法有效推动行动。 即便这个标准没有问题,依旧无法得出道德理由的形而上学怪异性。 就像作为一个概念问题,独角兽是像马一样有着神奇的角的生物。 在独角兽这一概念下,任何通常没有神奇的角的生物都不是真正的独角兽。 但这并不是说没有角的独角兽就是形而上学怪异性的。 其次,像道德理由这样的非目的性理由作为一种客观事实是不存在的。 就像人们否认孙悟空或是龙的存在。 但是,基本的道德理由需要我们扩展我们的本体论范畴。 这也引出了最后一个反驳,就是会产生麦凯提出的道德存在与宇宙中的其他任何东西完全不同的属性或是实体的问题。 [4]那么我们要如何感知和定义这种与其他事物都不同的属性和事实?
这里提到的CGA策略并不是从上述角度来对麦凯的论证进行反驳的,它主要是基于认知理由和道德理由的对等关系进行类比进行论证,从而为实在论辩护。 这一策略借鉴了麦凯给道德客观主义者提出的建议,即寻找和道德一样有问题的同伴立场。 像是通过将道德错论与认知错论或是数学错论进行对比,发现其对等性,从而反驳错论的核心观点。 认知CGA策略就是在预设认知错论与道德错论对等的基础上,通过论证认知错论的不可能性来证明道德错论是有问题的。 关于认知理由的CGA策略的具体论证如下:
(1) 根据道德错论,并不存在绝对的规范性理由;
(2) 如果不存在绝对的规范性理由,那么也就不存在关于信念的认知理由;
(3) 关于信念的认知理由是存在的;
(4) 因此,存在绝对的规范性理由;
(5) 所以,道德错论是错的。 [5]
上述论证蕴含了两个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道德错论的形而上学前提,即不存在绝对规范性的信念认知理由; 第二个前提是认知存在前提,主张存在一些明确规范性的信念认知理由。 很明显,道德错论的形而上学前提是错误的。 因此,对道德错论的论证是不合理的。 这一策略最大的优势在于它并不直接质疑它所针对的元伦理学论证的具体前提,相反,它阐明了这一论证的非道德后果。 同时,这一策略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些稳定的基础来评估元伦理学中的观点。 如果我们把元伦理学中的怀疑论论点概括为数学、逻辑或认识论相应的论点,我们就有明显的理由怀疑它们。 但是这一策略没有对道德形而上学或认识论问题提供积极的解释,仅仅表明了一些怀疑论论点的失败。 所以即使它成功地表明这些论点失败了,也不能表明错论失败的原因或情境。 此外,该论证的类比前提也是有问题的。 道德理由与认知理由可以被看做是不同的种类,就像认知理由可以仅仅是情境性的,类似于体育、游戏或礼仪所产生的理由。 如果这种说法是正确的,那么CGA策略关于认知错论与道德错论的对等前提肯定是不成立的。 [6]这样一来,从认知理由出发的对认知错论的反驳无法应用于对道德错论的批判。
二、 道德错论者对CGA策略的回应
对于CGA策略,道德错论者提出了一系列方案以辩护自身的合理性。 首先是构建一个不需要承诺关于认知理由的错论的道德错论,即不影响认知规范性的道德错论。 如果关于道德的事实和主张涉及关于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第二人称理由的主张,则不会导致关于认知理由的错论。 因为即使存在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理由,也不存在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第二人称理由,所以道德理由是不可能存在的。 而认知理作为一种非第二人称理由,则是可以存在的。 在道德错论者看来,我们有道德理由做a的事实不能用非规范性的事实来还原分析。 因为我们有道德理由去做的事情似乎超出了我们的欲望,以及我们社会的标准和惯例认为我们有理由去做什么的要求。 如果我们看到一个孩子在池塘里溺水,那么我们似乎有很强的道德理由跳进池塘去拯救他们,即使我们并没有这种意愿以及我们社会的标准并没有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 同时,我们还可以利用第二人称理由的机制来构建一个更加合理的道德错论版本,以回避CGA策略。 第二人称理由指的是我们有理由因为别人有权威或地位来满足其要求,就像军队中的军人有第二人称理由服从他们的军官,只是因为他们的军官具有的实际权力要求他们遵守命令。 可以说,第二人称理由本质上与规范性权力有关,这种规范性权力是指主体必须履行特定义务或改变其原因的权力。 所以,许多道德理由就可以被看做是第二人称的。 像是履行承诺的理由似乎取决于承诺者要求我们履行对他们的承诺的权威,而仅仅因为善而捐款这样纯粹基于价值的理由则不是第二人称理由。 同时,有许多认知理由不是第二人称的,因为它们是独立于实际的权威关系而存在的。 就像我们相信恐龙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并不来自于任何人的要求。 [7]550同理,如果我们有很强的证据可以证明p,那么我们就有很强的认知理由去相信p,而不需要他人的权威支持。 因此,第二人称理由依赖于实践权威关系以及规范性权力的存在,而认知理由并非如此。 此外,第二人称理由还可以为道德错论关于道德是第二人称的概念性主张做支撑。 因为第二人称隐含着一种要求(demand)态度,就此我们可以提出如下支持道德错论的反应态度(reactive attitudes)主张: 一个行为主体做a是不道德的当且仅当做a是道德上值得被谴责的。 这一主张的优点在于如果我们接受道德和积极态度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可以解释道德错误和被谴责之间的相关性,像是折磨他人这种道德上错误的行为为什么是值得谴责的。 同时,这一主张也使我们能够解释一个人做了道德上错误的行为和做了超义务的道德行为之间的区别。 超义务的道德行为就是那些我们有最多的道德理由去做的事情,而道德上有错的行为就是我们做了之后会受到谴责的行为。 可能会有人提出存在着无可指责的错误行为来反驳这种主张。 但是这一反驳是不合适的,因为我们可以接受道德上的错误必然与被谴责有关,同时也可以接受有些行为在特定情境中是不被谴责的。 就像为了让得了癌症的老人过得更加安稳而谎称其得的病并不是癌症这一行为就不应该被谴责。 此外,麦凯提出的怪异性论证也可以用来回应CGA策略。 如果我们认为除了描述性事实外,还有不可还原的规范性事实,那么就不可能有进一步的形而上学上的怪异性来认为存在着特定的不可还原的规范性事实,如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第二人称理由。 然而,这种反应并不能证明规范性事实没有任何明显的、规范性的、奇怪的或神秘的东西,或是它们随附于意志或意愿之上。 因此,道德错论关于道德事实和属性的怪异性论证就是合理的。 即使存在或可能存在不可还原的规范性认知理由,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的第二人称理由也可以是不存在的。 [7]553-560
其次,考伊(Christopher Cowie)还提出了一种关键论证(master argument)来反驳CGA策略。 他认为想要认知存在前提成立,就必须将认知理由理解为一种证据支持关系。 假设我看了火车站的通知屏幕,上面说我的火车在8点出发,那么我就有了相信火车8点出发的认知理由。 一般来说,不管自己的意愿如何,这个认知理由一定是关于我8点出发的绝对规范性理由。 但是考虑到错论者否认绝对规范性的认知理由的存在,但不会否认火车站的通知屏幕提供了关于相信火车8点出发的证据支持。 所以,为了使得认知CGA策略起作用,最好将认知理由理解为一种证据支持关系。 这一关键论证的核心论点在于:
(6) 只有当关于信念的绝对规范性理由就是一种证据支持关系时,认知存在前提在辩证语境中才能成功地建立;
(7) 关于信念的绝对规范性认知理由不是证据支持关系;
(8) 所以,认知存在前提在辩证的语境中不能成功地确立。 [8]115-130
然而,不管(7)是否为真,上述论证都是不成立的。 因为在辩证语境中建立认知存在前提需要将认知理由作为一种证据支持关系,但是认知信念的理由不仅仅是证据支持关系。 有许多关于“理由”的标准用法显然是非规范性的,像是游戏规则这类制度性的理由。 在这些情况下,一个人可能拥有一些相关的理由,而不具有规范性的理由。 假设我拥有并意识到拥有与命题p有关的证据e,但我没有兴趣就该命题达成一个真的或证据支持的信念,因为这样做对我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如果人们仍然认为e是我应该相信p的证据,而不仅仅是e是p为真的证据,那么他们肯定有很大的责任来解释其中的原因。 因此,从目前对规范性理由的理解来看,论证的责任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否认(7)的人,而不是接受它的人。 此外,即使认知理由的信念只是证据支持关系也是无用的。 因为这样一来,认知理由就可以还原为证据支持关系从而被看做是一种还原的规范性理由,而道德理由是不可能还原的,因此CGA策略提出的关于道德理由和认知理由是对等的这一前提就无法成立。
还有道德错论者在考伊的主要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对CGA策略的另一种回应,即主张知识包含非绝对性的认知理由。 “实际上有两种方法来考虑知识所带来的证明。 我们可以仅仅从证据支持关系的角度来考虑它,或者我们可以从绝对规范理由的角度来考虑它……认识论错论者会声称我们拥有某些信念的证据,但没有绝对的规范性理由去持有这些信念。 所以,我们确实有知识。 ”[8]119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认可某种形式的认知主观主义来回避CGA的批判。 就像胡西(Stan Husi)提出指导哲学讨论的认知规范即使不被证成为真也可以作为实现我们目标的工具或策略。 [9]但是这一回应受到了很多批判。 在正确的辩证语境中,道德错论者无权否认绝对的规范性理由的存在,因为这只是乞题而已。 同时,这一回应明显是反直觉的。 因为从日常生活来看,关于认知规范的确存在一些权威的、明确的或客观的东西。 最后,这一回应还具有辩证不连贯的问题。 因为它表明在哲学背景下,错论者没有理由接受他们实际上接受的立场。 然而,就像表达主义者提供了一个连贯的解释,它意味着什么是承诺的规范,从而解释了他们认为自己正在做的是什么。 在考伊和胡西为他们对错论的首选解释提供论据的同时,他们也提供了对他们自己的哲学实践的元规范解释,而这些解释并不使他们相信绝对的认知理由。 所以,这一回应是具有可行性的。 还有一种参考了考伊论点的回应是乔伊斯(Richard Joyce)针对CGA提出的关于理由的论证。 他首先提出认知CGA的前提错误地将错论的立场与它的论点混为一谈。 就像无神论者可能会认为邪恶的存在表明上帝不存在,但无神论者不需要支持这一论点,因为无神论者本身并不支持任何关于上帝不存在的特殊论点。 之后,乔伊斯提出了一种来自理由的论证:
(9) 如果X在道德上应当去做a,那么不管其意欲和兴趣如何,X都应当这么做;
(10) 如果X在道德上应当去做a,那么X有理由做a;
(11) 因此,如果X在道德上应当去做a,那么不管其意欲和兴趣怎样,X都有理由这么做;
(12) 但是并不存在构成这种理由的事物;
(13) 因此,X不曾有过道德责任。 [10]
考虑到该论证仅限于讨论行动的理由,所以前提(12)只是声称不存在明确的规范性行动理由,而承认在认知领域存在着绝对的规范性理由也不会对错论者关于理由的论证造成损害。 一个人可能因为道德的某些品质在本体论上看起来很奇怪而成为错论者。 但是,我们目前正在考虑的错论论证已经远远超出了仅仅发现一些奇怪的东西,或许没有什么特别奇怪的绝对规范理由本身。 当涉及到实践理性时,似乎只有工具主义是真实的。 所以,并没有理由假设道德错论必然导致认知错论。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拒绝前提(2)来为道德错论辩护。 因为即使道德话语必须涉及绝对理由,认知话语也可以不涉及,二者并不是等同的。 认知判断表达的是心灵的意动(conative)状态,即一个人应该相信p表达了一些类似同意形成这种信念的东西。 它没有表达一种具有规范内容的信念,当然也没有表达一种关于有什么绝对理由相信的信念。 [11]此外,从现实来看,即便接受错论的观点,我们也不太可能完全放弃道德话语和道德判断。 我们仍然会关心自己生活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仍然会认为恐怖分子是错的,以及赞赏那些把一大笔收入捐给慈善机构的人。 即便我们的主张不再被当做是道德评价,但它仍然可以是一种实用的评价。 [12]总的来说,道德错论并不意味着必然拒绝认知规范或是认知理由。 我们还可以借鉴类道德化(shmoralising)的概念来发展一种类认识论,从而保留承诺认知理由的道德错论。 从现象学来看,道德化和类道德化看上去是差不多的,所以可以假设我们是一直在类道德化。 即使放弃了认知判断,还可以通过现成的认知词汇来传达这种类认知(shmepistemic)的判断。 但是,归属感的需求会要求行为主体拥有一种更强的真实的道德感。 我们需要体验出于道德理由而做出的选择,而根据认知原因形成的信念也是如此。 毕竟,在那些任意选择信念的人看来,她们的行动和判断似乎缺乏为规范生活提供稳定基础的那种基础。 然而,类认知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我们中的一些人显然否认有任何独立的绝对权威,也许她们会觉得自己可以走自己的路是一种解放,也可能是一种生命的肯定。 她们面临的唯一限制就是自身认可的那些限制。 同时,认知规范的问题未能使我们必须认为它是虚假的。 更一般地说,如果某一特定理论的哲学论点或反对某一特定理论的论点依赖于某些直觉或现象学的考虑,那么它也只会对那些分享相关直觉或现象学的人施加理性压力。 而那些在直觉或现象学上有差异的人不会受到任何理性的压力来接受这个结论。 这一结果有助于道德错论者处理认知规范问题,一个有上述的直觉的人不会受到任何否定道德错论的理性压力。
三、 对道德错论者回应的反驳
虽然道德错论者关于CGA策略的回应和反驳有一定的效果,特别是对其论证前提的批判和类认知途径的提出。 但是关于错论者针对CGA的对等前提(parity premise)采用的“差异回应(disparity response)”的方案其实是有缺陷的。 错论者拒绝承认道德理由和认知理由之间的假定对等,并声称虽然前者是不可还原的规范,但后者并非如此。 奥尔森(Jonas Olson)就声称认知主张可以还原为关于信念的态度是否符合他们的功能的主张。 但是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 因为功能理由是一个共同属的物种的标准理由,既然反对道德还原论的权威论点适用于标准理由,那么它同样也适用于功能理由。 而且CGA策略中的认知指南并没有证明错论的谬误,只是说错论的差异回应这一方案失败了。 此外,考虑到我们的日常道德话语和认知话语需要两种意义上的解释,即关于当我们说出道德或认知语句时,我们认为我们正在做什么以及我们需要解释我们做的是否成功。 第一个解释需要探索我们对这些话语的常识概念及其权威性。 而关于第二个解释,需要考虑两种不同的立场: 一是道德错论的立场。 主张我们的日常道德话语涉及到对道德理由的不可还原的规范性承诺,但是这种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理由并不存在。 而认知错论是对道德错论的一种认知模拟,认为我们的认知话语具有相同的系统本体论错误。 二是还原论的立场。 这一立场主张道德理由是存在的,而且是可还原的规范性的。 [13]因为“理由”在不可还原和可还原之间是模棱两可的,所以可以把理由分为两种可还原的理由: 假言的和约定的。 假言的理由被理解为可以还原到关于主体的欲望和实现他们满足的手段的经验主张,而约定的理由可以还原为关于什么是符合或违反公约的主张。 这样来看,认知理由是否可还原就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 就像对于姚明是否应该参与篮球活动这一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由适用于他。 而不可还原的理由是否适用并不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就像道德理由的不可还原性使其可以发挥促进合作等功能。 [14]所以,认知理由和道德理由并不像CGA所论证的那样是对等的。 然而,这一新的论证也存在不足。 因为我们有理由怀疑信念的功能是否真的能准确地表征现实,而道德理由也不一定是不可还原的规范性理由。 就像道德判断应该促进社会合作,还是主体有理由确保这样做,这依旧是一个开放性问题。 所以,关于不能建立道德理由的类似解释的说法并未得到支持。 [15]此外,考伊的关键论证也是不足的。 我们可以将这一主张根据对等前提扩展为如下论证:
(14) 只有当关于信念的绝对规范性理由是证据支持关系时,认知存在前提在辩证语境中才能成功地建立;
(15) 关于信念的绝对规范性理由并非证据支持关系;
(16) 认知存在前提不能成功建立;
(17) 然而,假设关于信念的绝对规范性理由是证据支持关系;
(18) 则关于认知理由与道德理由对等的前提则为假;
(19) 要么认知存在前提不能成立,要么对等前提不成立;
(20) CGA策略失败了。
一旦人们接受了这一论证的核心观点,考伊的关键前提以及他反对CGA策略的整个主要论点就崩溃了。 鉴于证据支持关系被认为是完全非规范性的,所以前提(14)明显是在本质上绝对规范性的认知理由的存在施加了一个不合理的必要条件。 同时,考虑到关于绝对性理由是否存在是有争议的,所以错论者无权以它为前提。 特别是无权在将必要条件强加于前提(1)中所表达的认知理由的前提下。 然而,如果没有这种前提,就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只有当认知理由是非规范性的证据支持关系时,它们才存在。 [16]而且,只要指出任何明显的反例,就可以对认知存在的前提作出强有力的推定。 例如火车站站长说下一班去上海的火车将于8点开出就足以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假设案例来建立关于认知理由存在的前提,而这一前提并不需要提及认知理由的绝对属性。 所以,关键论证对CGA策略的反驳是不成立的。
四、 余 论
总的来说,道德错论的核心观点确实受到了CGA策略的攻击。 特别是当道德错论者遇到一个道德客观主义者时,道德客观主义者的辩证优势的将会成为焦点,因为它有认识论和形而上学的价值,这与作为一个反对实在论的立场而产生的错论非常不同。 同时,错论者也不能识别客观主义者认知框架内的任何内部错误,因为每个论点都完全遵循客观主义者明确认可的逻辑系统。 错论者除了对客观主义者对认知价值的选择提出质疑外,无法找到任何批评道德客观主义者的方法。 因此,错论者需要谨慎对待他们批评道德客观主义者的方式,并诚实地对待这些批评的范围。 此外,在最近发表的关于CGA策略的文献中,错论者和道德客观主义者似乎都高估了他们的论点的力量。 因为错误是任何形式的客观主义关于任何一组主张的必要条件。 因为存在正确或不正确应用的非模糊条件是所有概念的一个必然特征。 就像伦理学中客观主义者与主观主义者之间的各种争论,并不完全归结为在这个意义上是否存在有意义的伦理学概念的问题。 同时,错论者关于道德与其他事实的区分的合理性也有待考量。 虽然CGA策略不能确定错论的虚假性,因为错论的反应不是质疑,不会破坏自己,也不会屈服于它具有违反直觉的后果的指控。 但是,在阐述道德错论和其反驳策略的过程中,可以发现一些无法忽视和避免的问题,例如认知存在前提和类比论证的合理性。 一种从审慎话语出发的类比论证似乎能够证明这一点。 其具体论证如下:
(21) 审慎对等前提: 如果道德错论的论据足以证明道德错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论据或它们的适当类似物就足以证明审慎错论是正确的;
(22) 审慎存在前提蕴涵审慎错论是错的这一结论;
(23) 因此,道德错论的论据不足以证明这一理论是正确的。 [17]
为了支持前提(22),似乎不可否认有些事情对人们来说是好的或坏的,有些结果对某些人来说比其他人更好或更坏。 但是这一前提并不预设任何关于审慎价值的特定实质性论点。 它仅仅依赖于一种说法,即某物对人是好的或是坏的,因而不需要受本体论承诺的约束。 这种审慎类比论证比之前的认知类比论证要更为严谨,因为审慎的论点比认知的论点更为全面。 虽然二者在第二个评估标准上是接近相等的,认知错论要求没有任何信念比另一个信念更合理,而审慎错论也要求同样的主张,即对一个人来说,没有任何结果比别人更好或更坏。 但从第一个评估标准来看,审慎的论点更具优势。 这是因为将知识属性还原为真理属性是可能的,但对审慎话语来说并不存在这样合理的还原。 所以,对比认知话语来说,审慎话语更接近于道德话语,用来反驳道德错论也更合适。 然而,审慎理由和道德理由是否具有完全的对等关系依然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考虑到上述原因,认真对待CGA策略不仅有助于道德错论者进一步思考错论的认识论问题以及一阶道德实践的可行方案,还可以为道德实在论者稳固自身提供更多的论证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