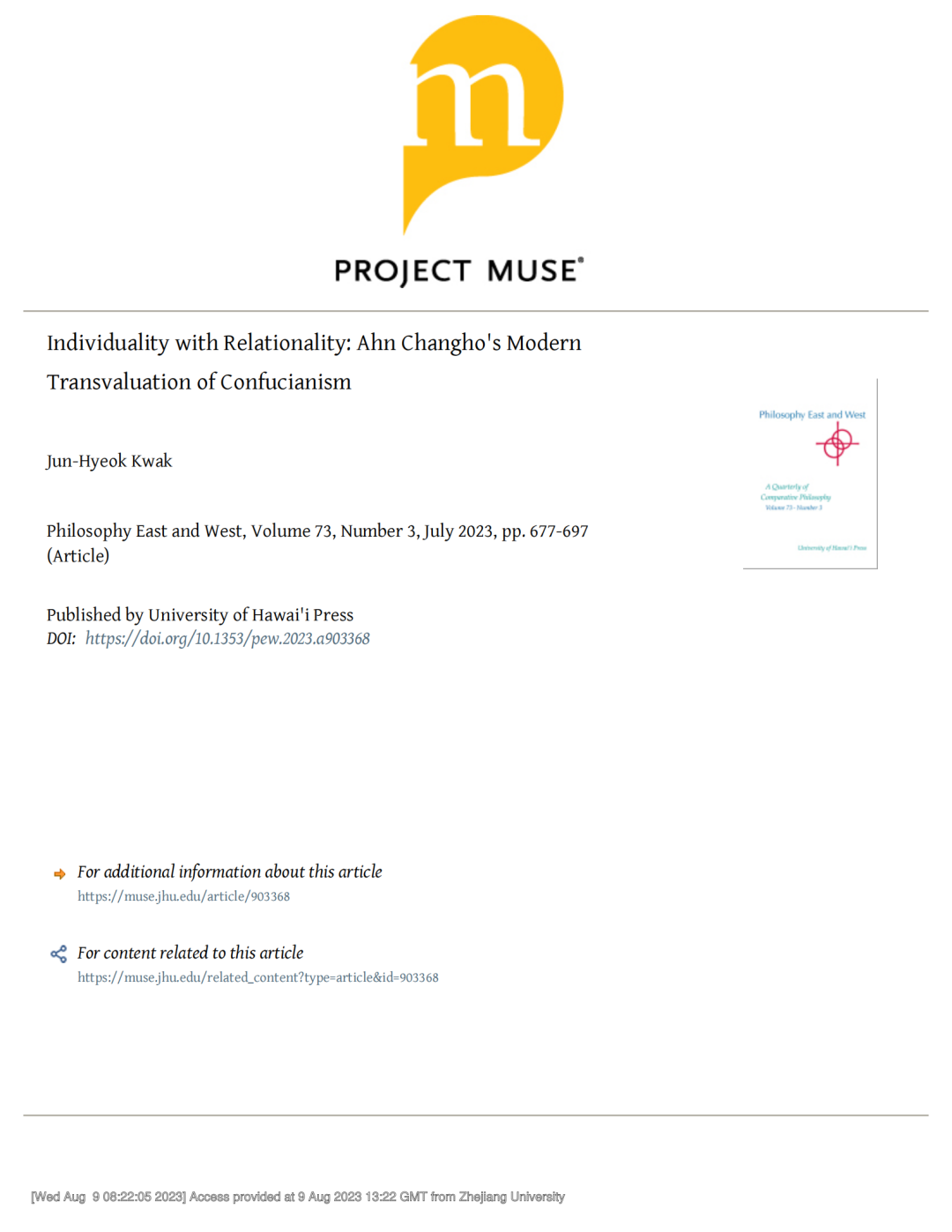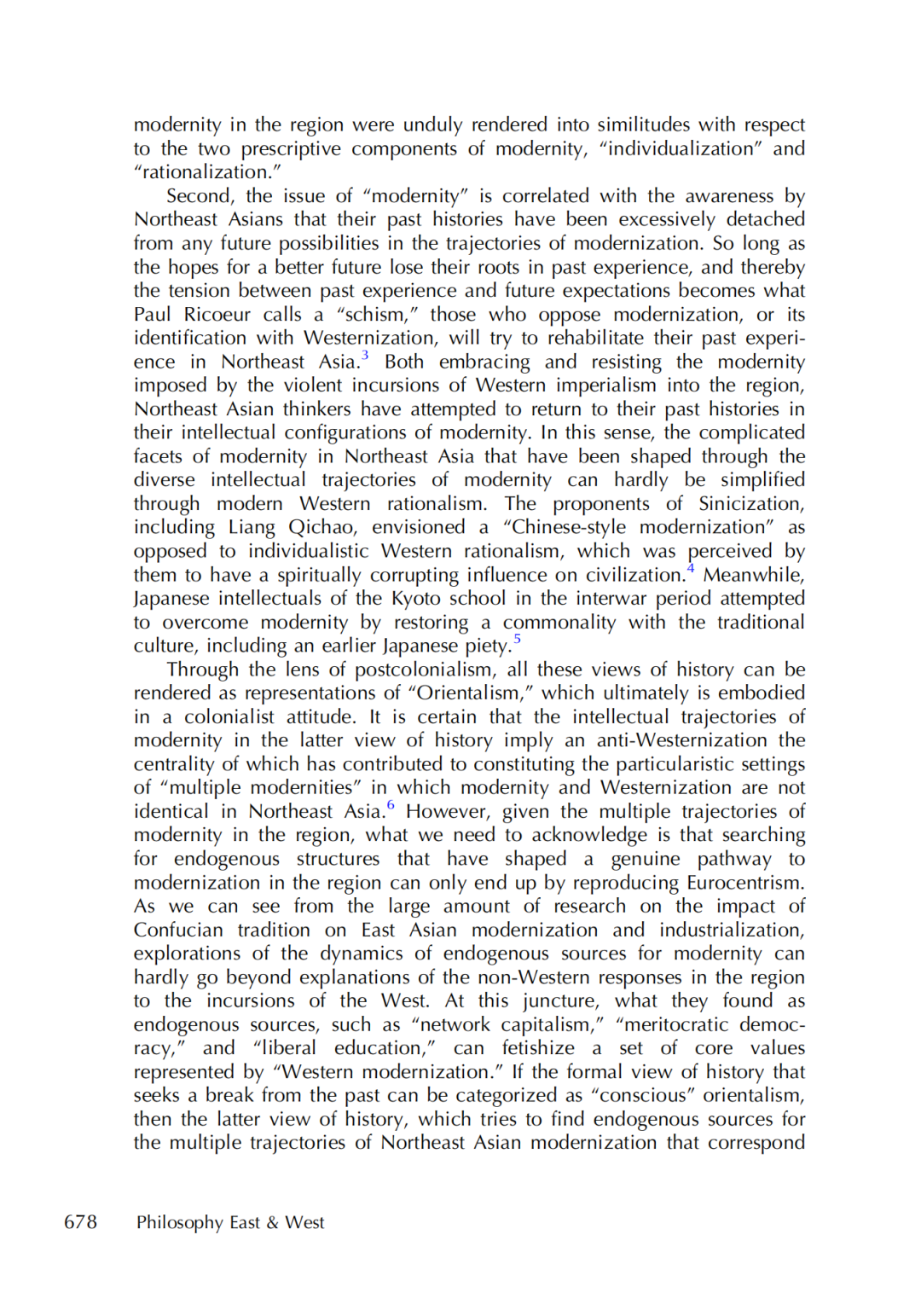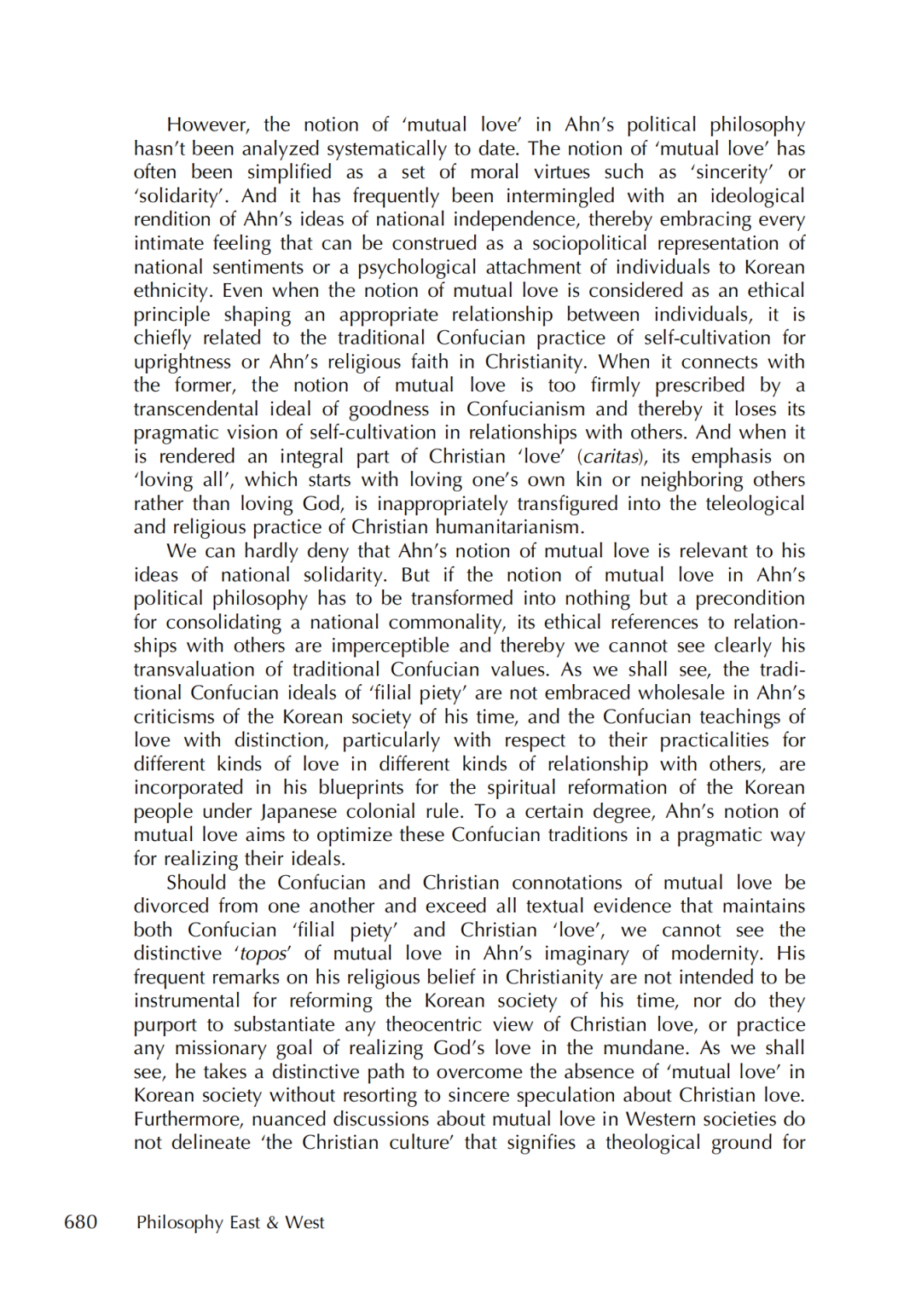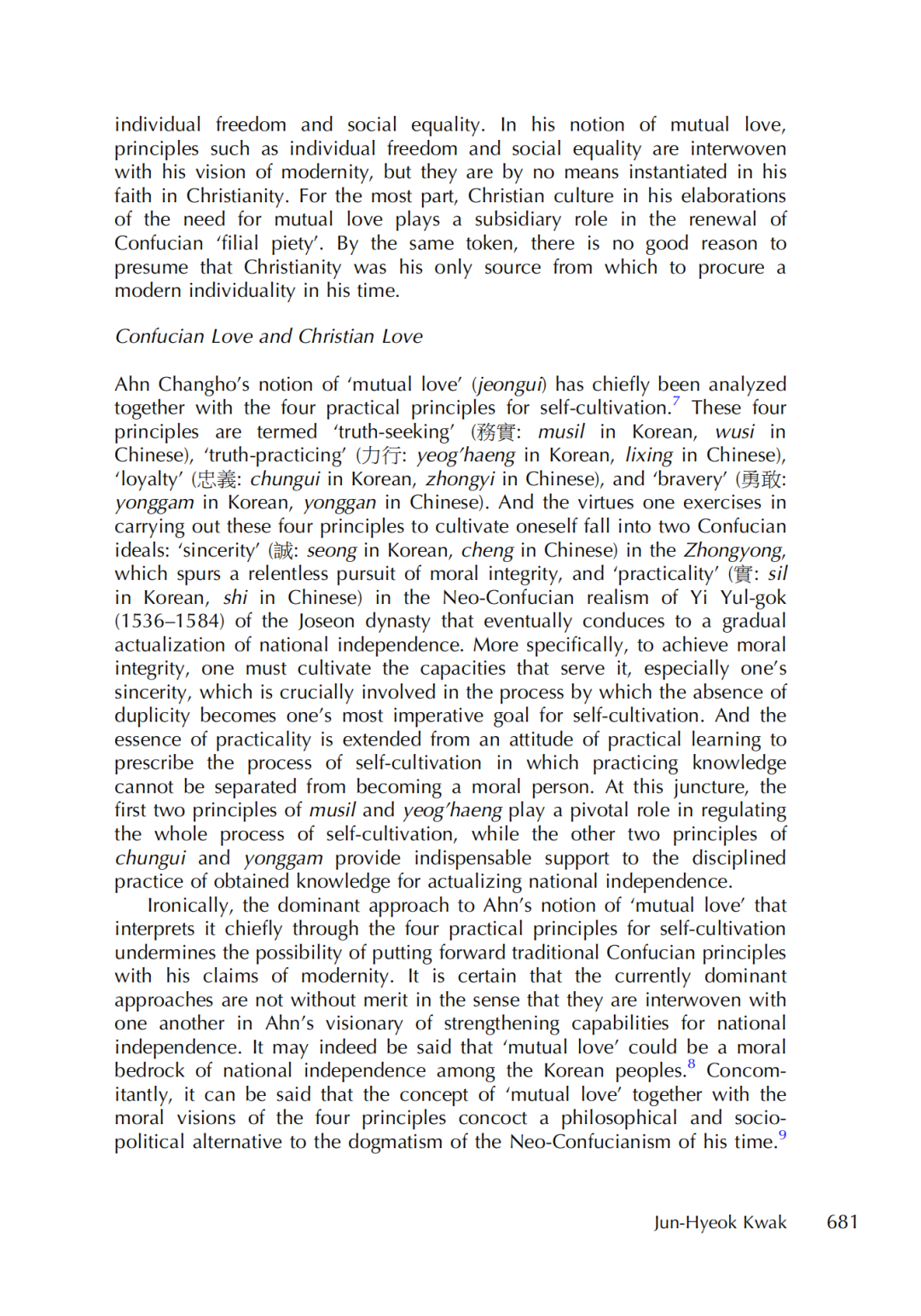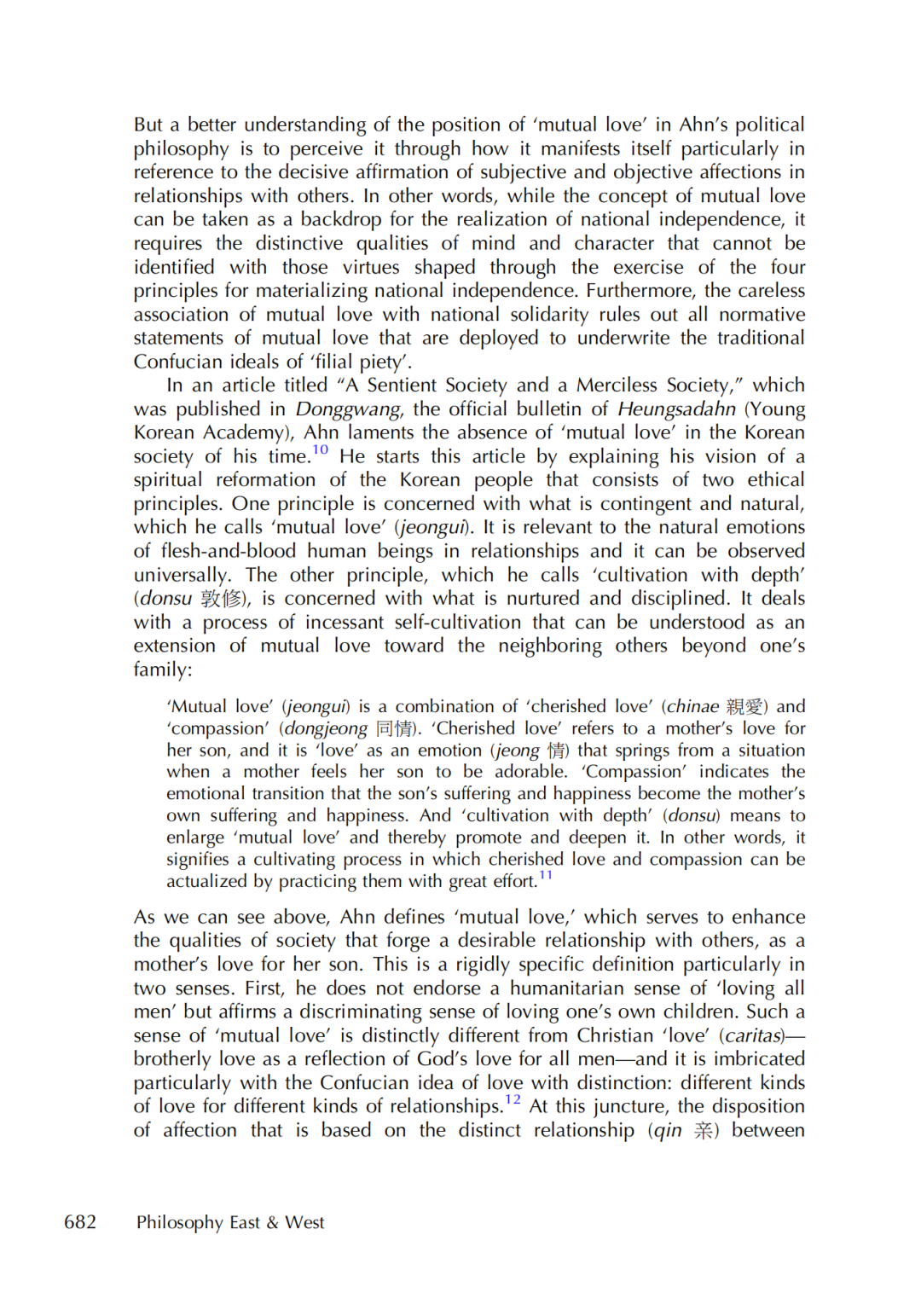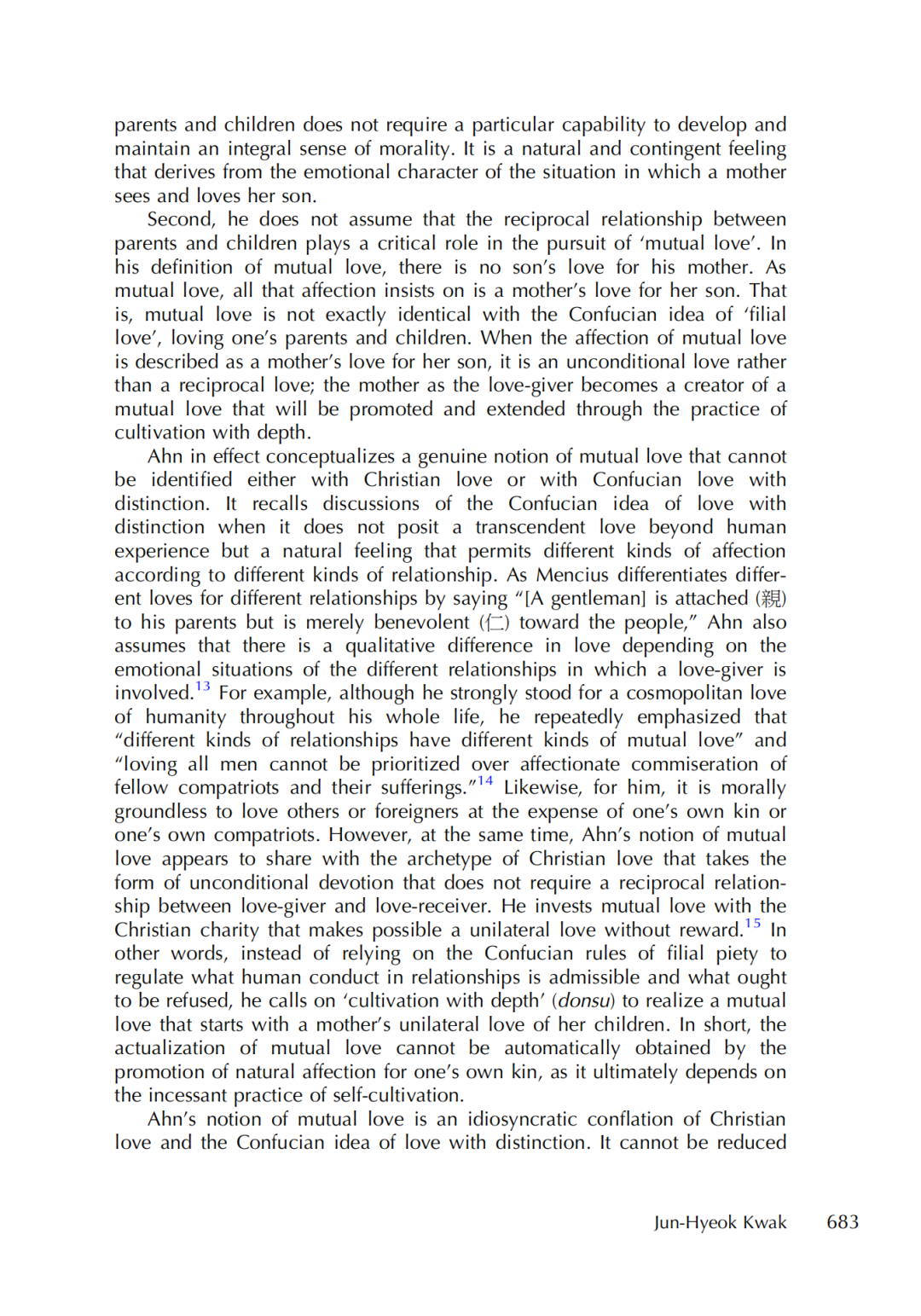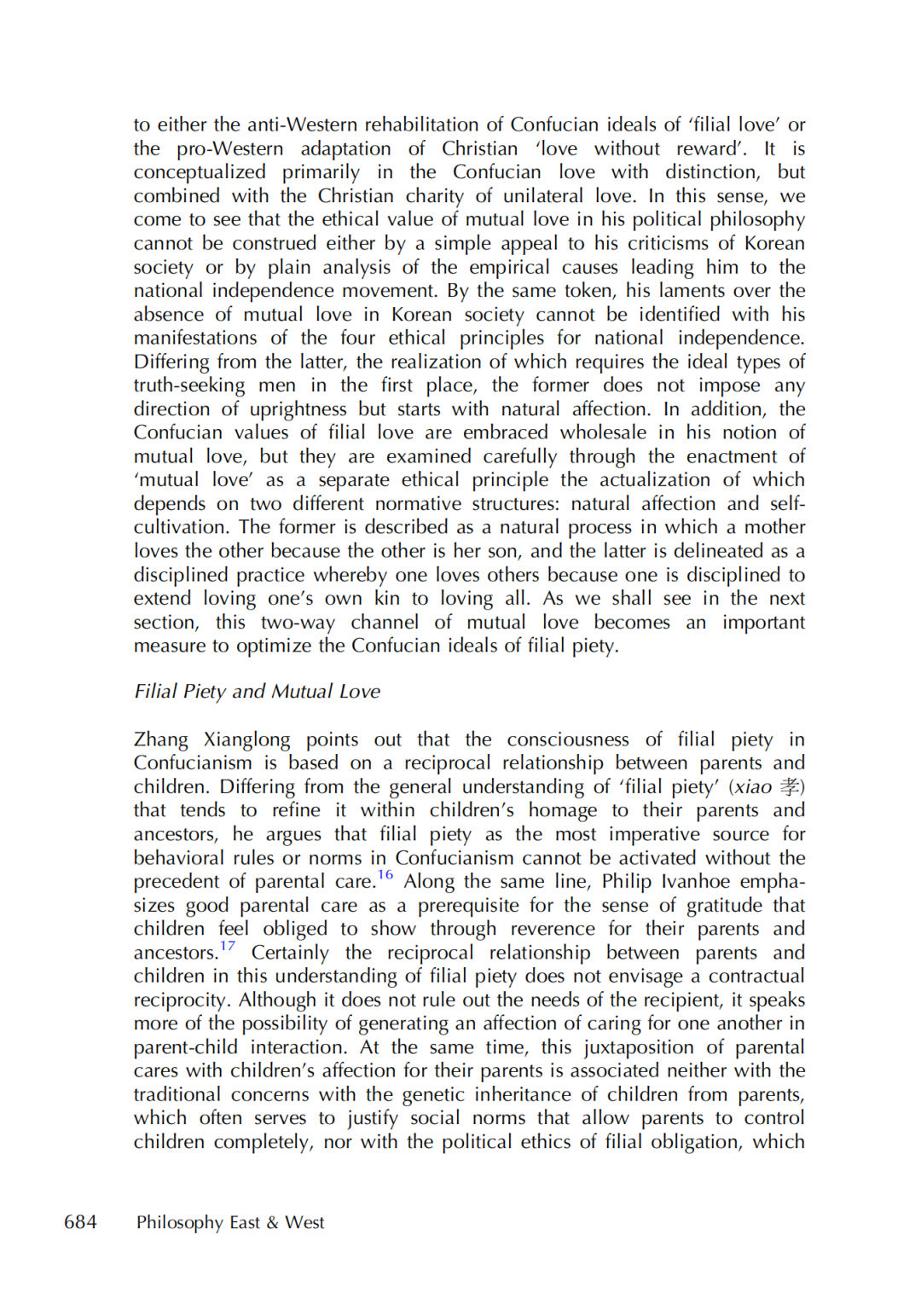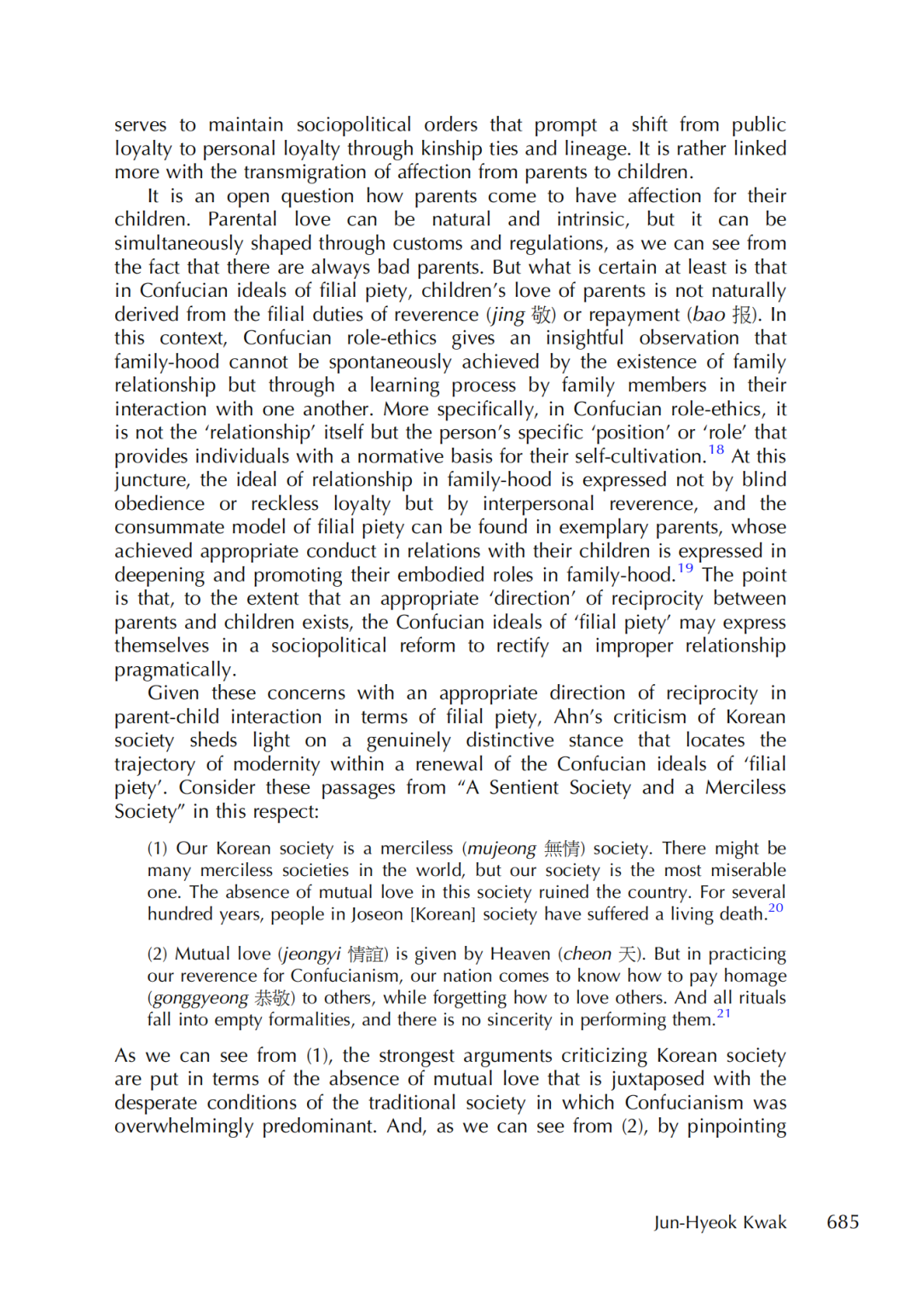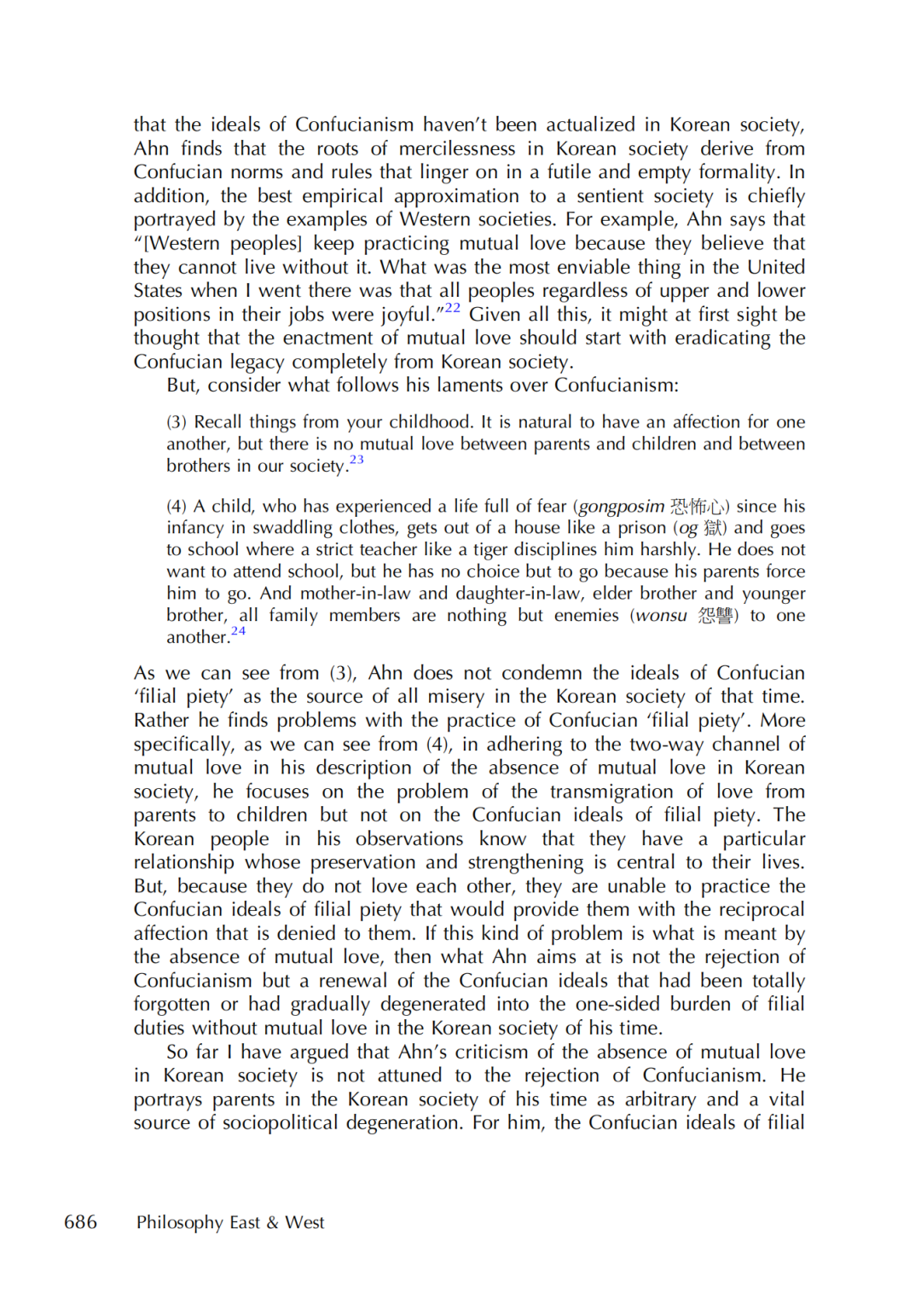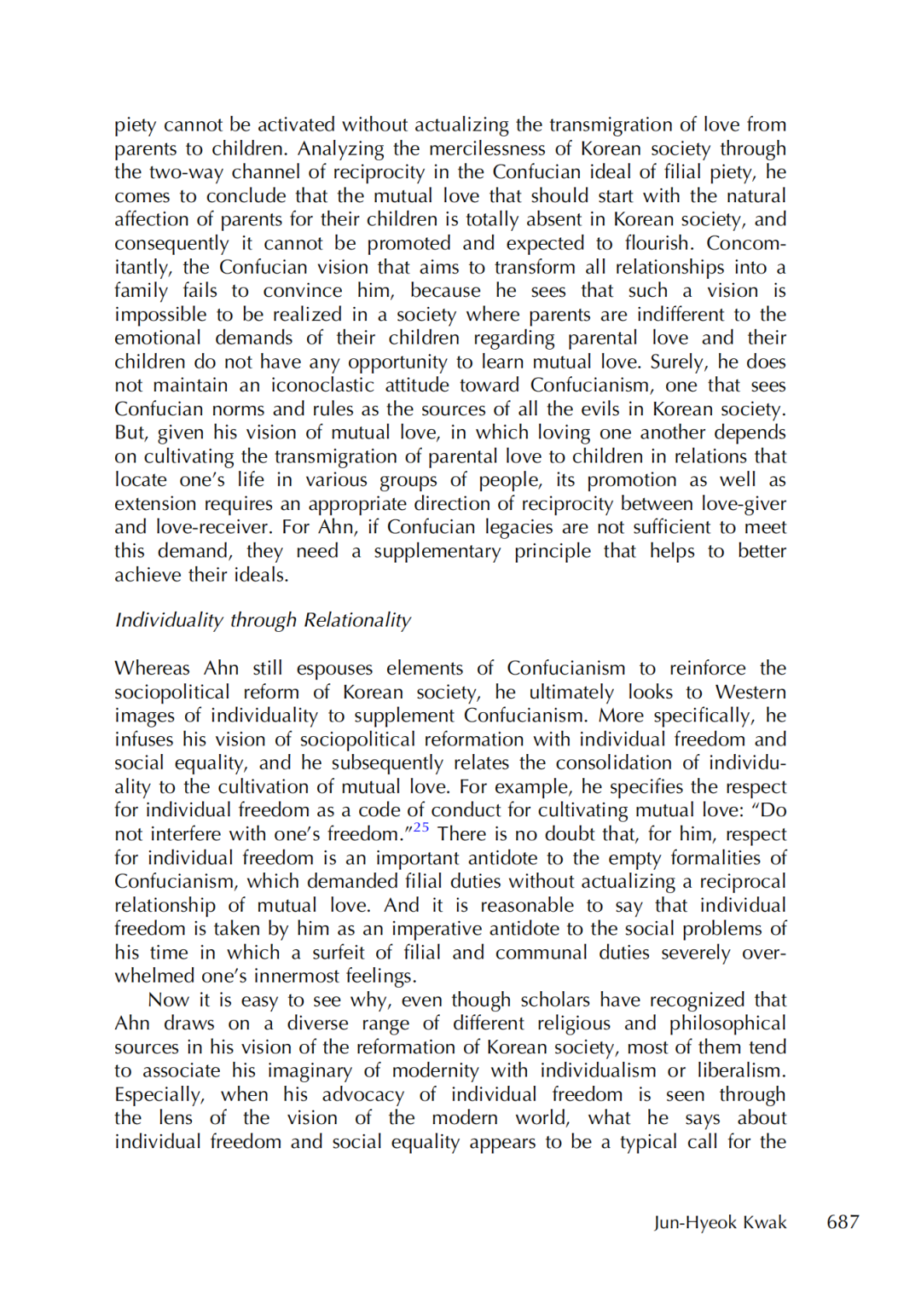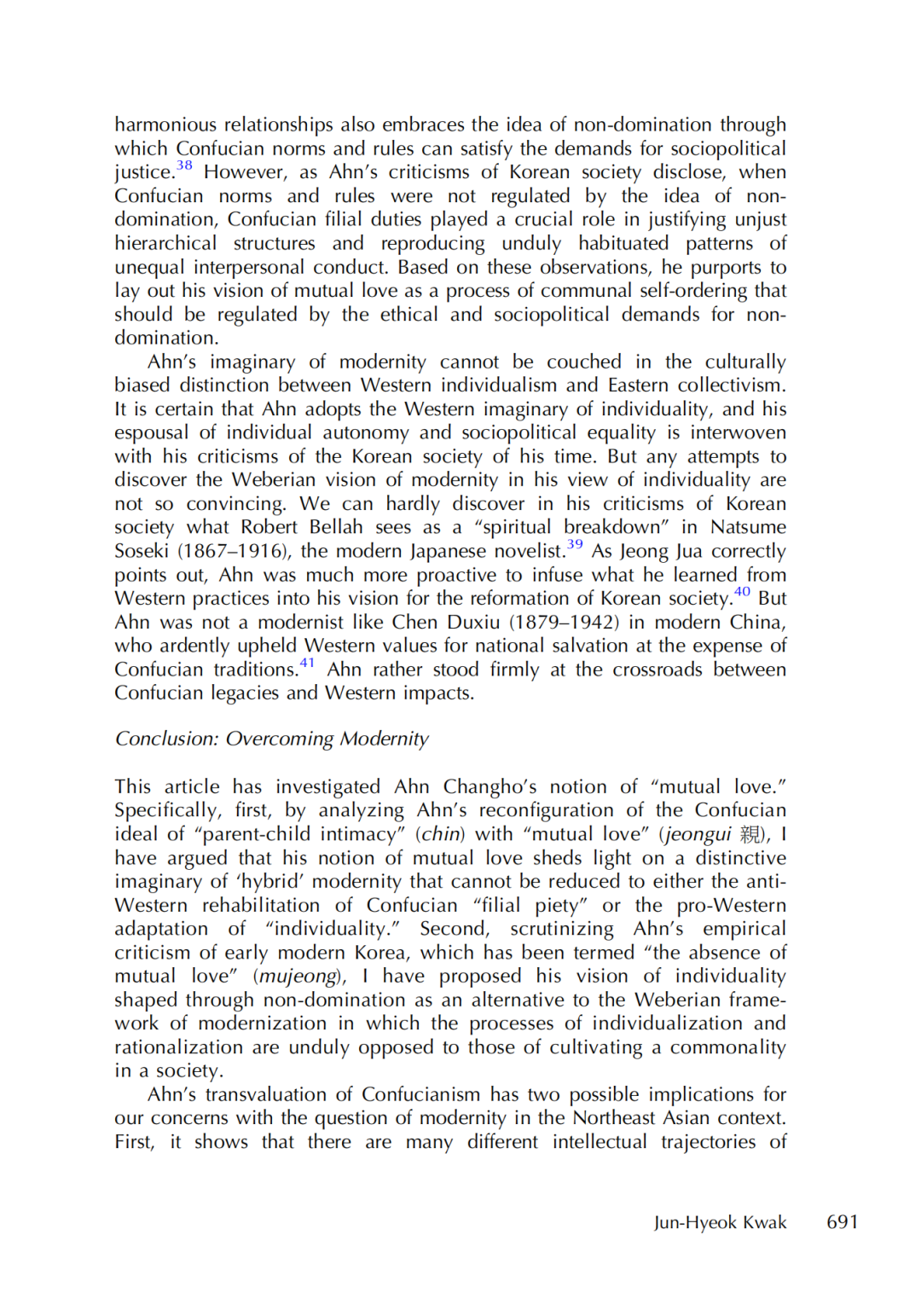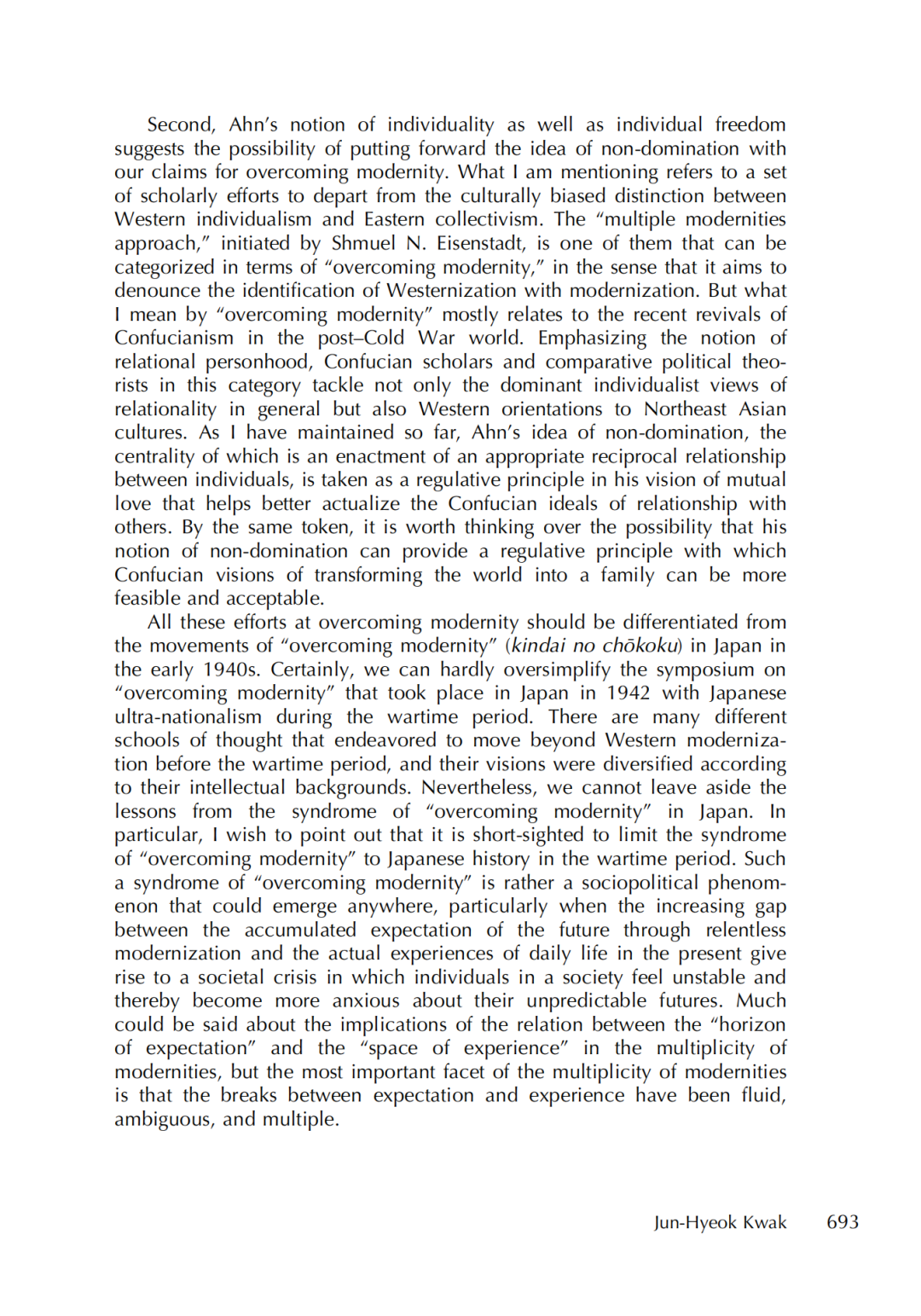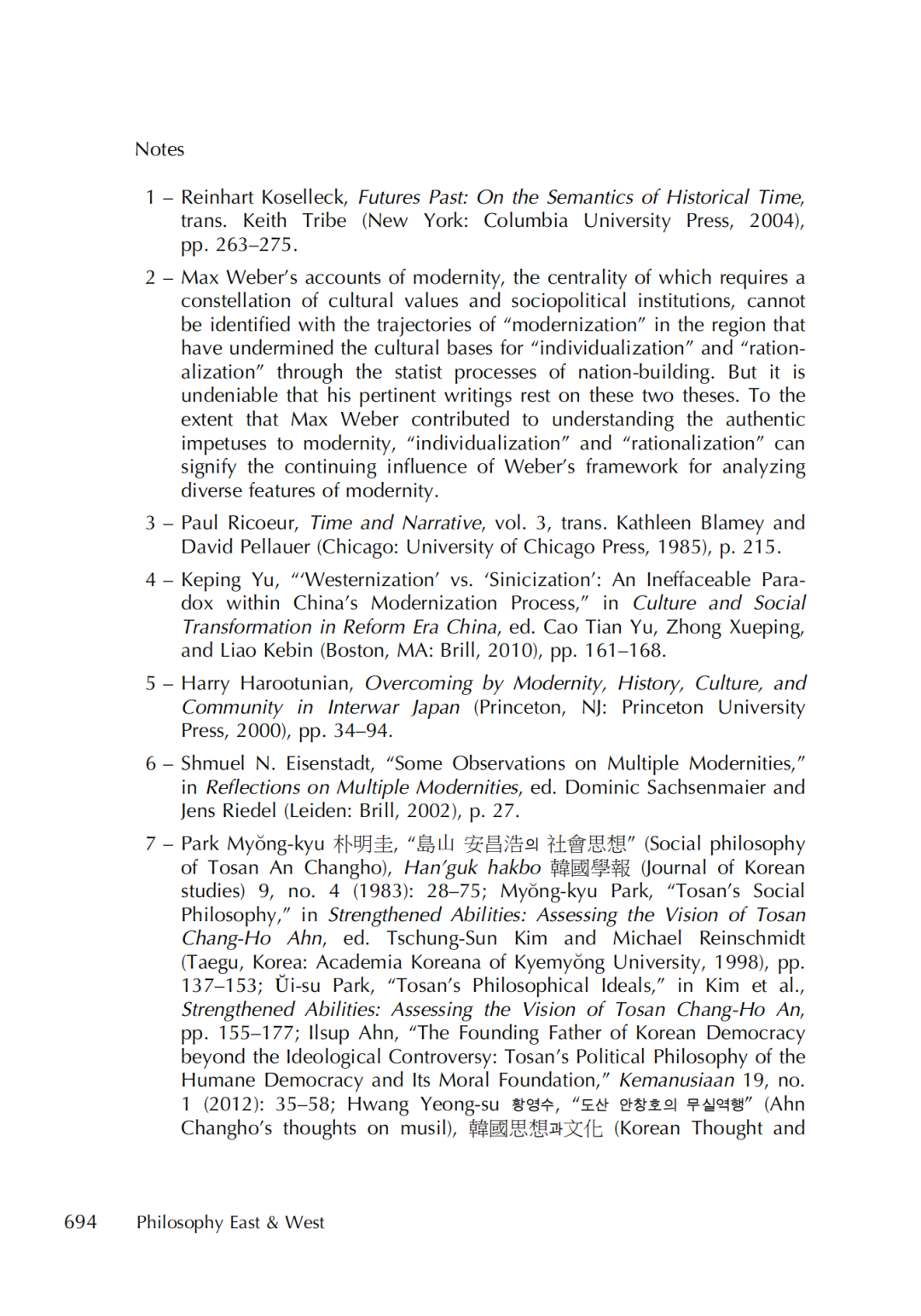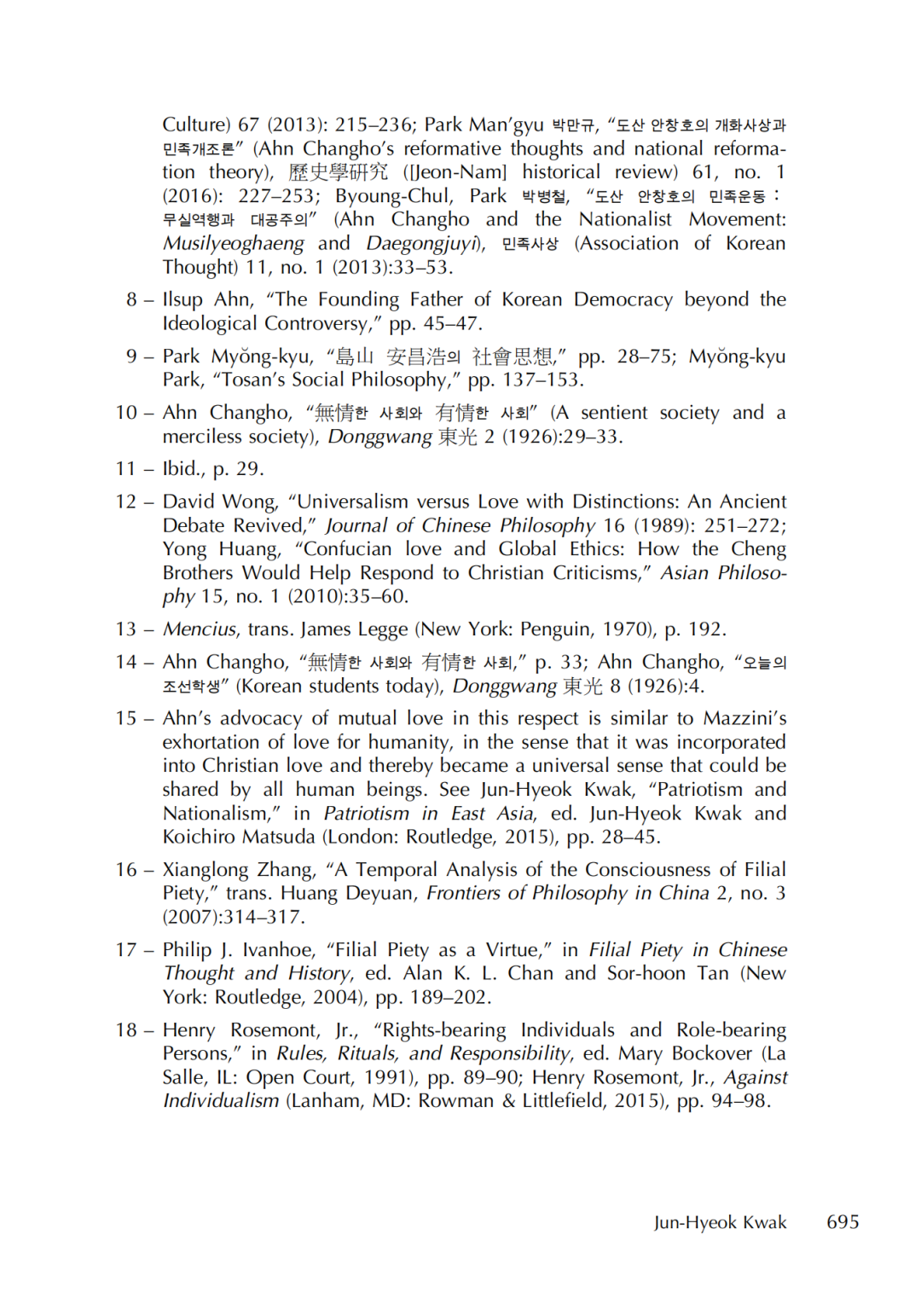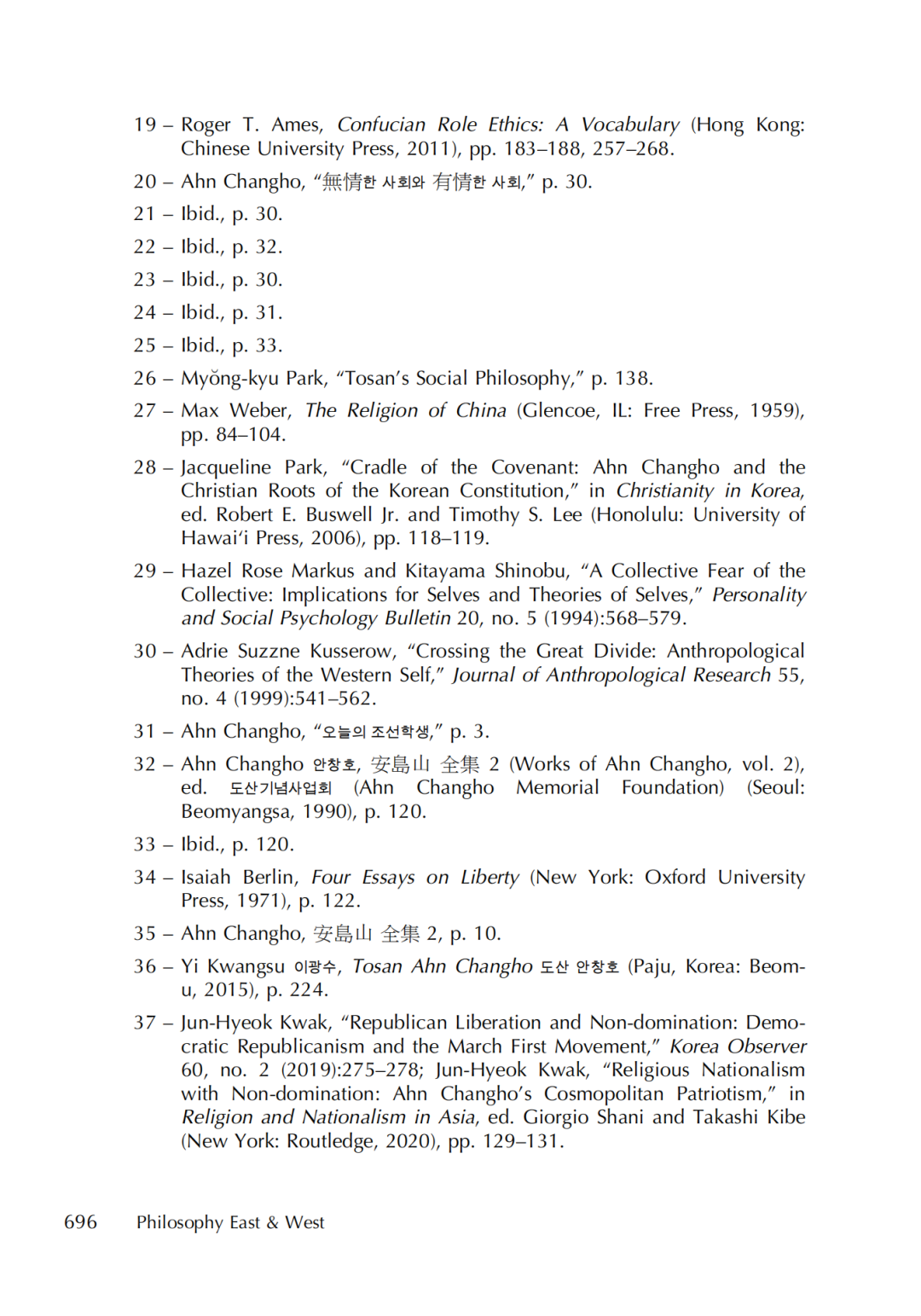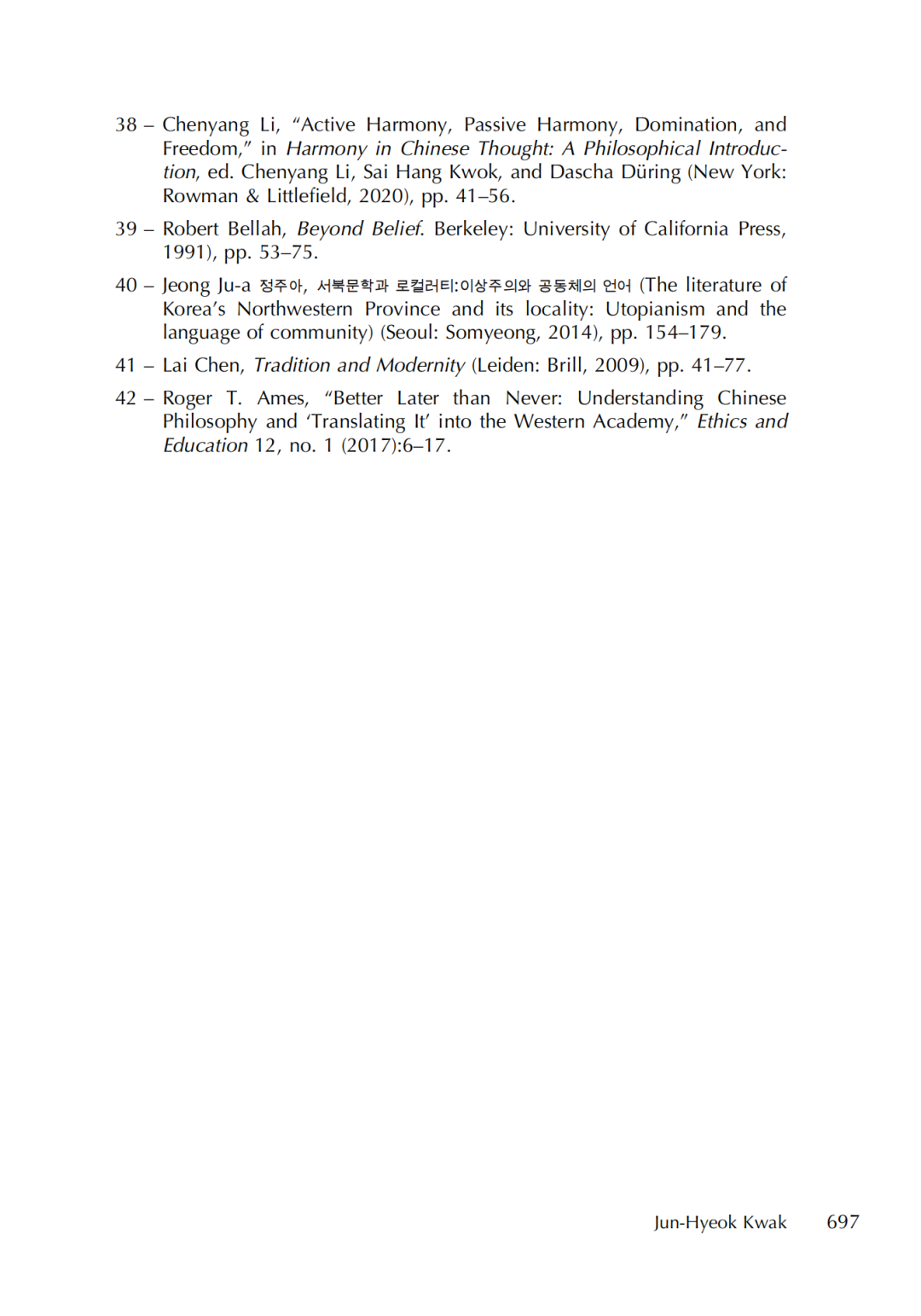学术资讯 | 我系郭峻赫教授文章发表
Title:Individuality with Relationality: Ahn Changho's Modern Transvaluation of Confucianism
Journal: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Journal pic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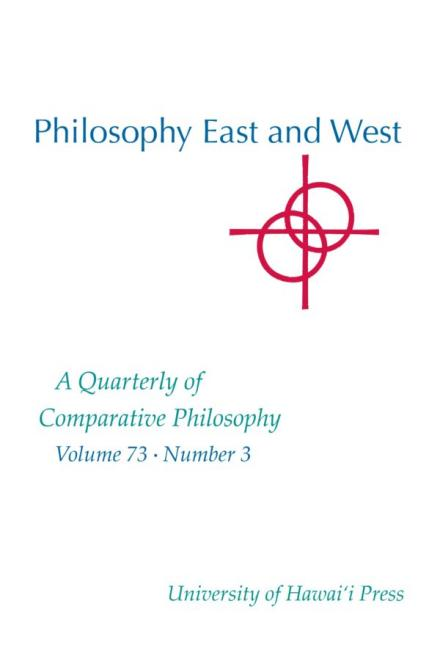
Web-Posting (Full Text): https://muse.jhu.edu/article/903368
Website of the Journal: https://uhpress.hawaii.edu/title/pew/
文章摘要Abstract :
个体性与关系性
在东北亚,现代性(modernity)是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术语,因为其无法准确反映出伴随着19世纪西方的侵入,东北亚所发生的文化剧变和社会政治的变迁。以故,它不仅指在启蒙和技术进步的意义上对西方的学习,还指向通过社会政治和思想的运动对西方的克服。该地区面对现代性浪潮的两种不同回应体现在东北亚诸国独特的社会政治实践之中,并根据特定的时代和语境发展至今。毋庸置疑,最近在该地区寻找现代性内生根源的努力,同样与这些多样化的现象有关。在这些现象中,对由现代性所导致的变化的肯定与否定塑造了该地区现代性的不同轨迹。
与此相随的是,东北亚的“现代性”议题与不同的历史观交织在了一起。首先,这一议题始终与莱因哈特·科塞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曾称之为“经验空间”(Erfahrungsraum)和“期望视界”(Erwartungshorizont)之间的关系的断裂具有相似性。此种断裂阐明了对未来的期望和经验所形塑的视野之间的分离。(Koselleck, 2004: 263-275)正如我们在1919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中所见,“启蒙”的概念与一系列特定的评价性理想(evaluative ideals),如“个人自由”,相关联。故而,它被用于辩护过去和未来之间不可避免的决裂。在其中,该国的传统规范或价值被认为是科学的或文化的不成熟,将会阻碍朝着更加美好的未来的合理进步。秉持这种历史观的人同时常常强调现代化进程即为“西方化”(Westernization)。在此处,现代性指的是在韦伯框架内迈向个人主义的和理性化的进步,即个体从社会关系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于他人的个体,而国家则转化为法治之下的理性化治理。出于同样的原因,就现代性的两个规定性构件(prescriptive components)分别是“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和“理性化”(rationalization)而言,该地区现代性的多样的思想轨迹被不恰当地呈现为此种相似物。
第二,“现代性”的议题与东北亚人们的一种意识相关,即他们意识到,在现代化的轨迹中,他们过往的历史与任何既定当下的未来可能性过分脱节了。只要对美好未来的诸般希望丧失了它们植根于其中的历史经验,就会导致历史经验和未来期望之间的张力变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85: 215)所称的“分裂”(schism)。进而在东北亚,那些反对现代化,或反对将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人就会努力尝试复兴他们的历史经验。对于随附西方帝国主义对该地区的暴力侵入而输入的现代性,东北亚的思想家们在既抱持又抵触的同时,力图在他们自己对于现代性的思想构造中回归历史。在这个意义上,东北亚现代性的复杂面向是通过现代性的多样的思想轨迹所形塑的,难以用现代西方的理性主义加以简化。中国化(Sinicization)的支持者,包括梁启超在内,设想了一个“中国式的现代化”,与个人主义的西方理性主义相对。后者被他们视为精神堕落的文明(Yu, 2020: 161-168)。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时,京都学派(Kyoto school)的日本知识分子曾希望通过诉诸传统文化之中的共性(commonality),例如早期日本的忠孝(Japanese piety),来克服现代性(Harootunian, 2000: 34-94)。 在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的视角下,上述历史观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表现,最终导向的是一种殖民主义的态度。可以肯定的是,后一种历史观中现代性的思想轨迹潜在地指向反西方,其核心有助于构建“多重现代性”(multiple modernities)的特殊主义的环境。于其中,东亚的现代性和西方化不是相同的(Eisenstadt, 2002: 27)。然而,考虑到该地区现代性的多重轨迹,我们需要承认的是,寻找塑造了该地区真正的现代化之路的内生结构,可能最终会复制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正如我们从大量关于儒家传统对东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影响的研究中所看到的那样,对于现代性的内生根源的动力的探索,几乎难以超越该地区针对西方冲击做出非西方回应的解释框架。因此,他们基于此所发现的所谓的内生根源,例如“关系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贤能政体”(meritocratic democracy)或“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可以契合一套以“西方现代化”为代表的核心价值理念。如果说,前一种寻求与过去决裂的历史观可以被归为“有意识的”(conscious)东方主义;那么后一种历史观由于试图为东北亚现代化的多重轨迹寻找内生根源,以对应于西方现代化的核心价值,故而可以被归为“无意识的”(unconscious)东方主义。
基于上述考察,本文将探讨安昌浩的“互爱”(mutual love)概念,其核心特征呈现为一种“混合的”现代性,在其中传统的社会理想并未被通盘接受,而是通过现代性理念的谨慎运用而得到重新表述。更具体地说,安昌浩的“互爱”概念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对儒家的“孝道”(filial piety)的“实用主义的”(pragmatic)最优化。这一对儒家思想的“重估”构成了安昌浩呼吁韩国进行“精神改革”(spiritual reformation)的基础,并导向了对现代“个体性”(individuality)的独特理解。基于此,在安昌浩对于韩国社会的批评中,其核心是儒家传统的孝道理想在一个缺乏互爱的“无情的”社会中已经沦为一种“空洞的形式”(empty formality)。但他的解决方案既不是回归传统的儒家实践,也不是盲目地拒斥和根除其原则,而是以一种可以说是现代的形式更新和复兴儒家理想。在这一层面,安昌浩将互爱的伦理植根于“个体的自由”(individual freedom),而不是基于对血缘或社群的责任的外部准则,从而将“非支配”(non-domination)的伦理要求引入了儒家传统。与此同时,他的“个体性”概念是在儒家宇宙论中的关系认识论的基础上进行阐述的,因此区别于与西方个体主义相联系的“原子式自我”(atomic self)。(翻译:杜陈)
作者简介:

郭峻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2002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毕业。曾任职于韩国高丽大学、韩国庆北国立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研究领域是政治哲学、当代政治理论和比较哲学。特别关注但不限于从古典共和主义资源例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和马基雅维利的政治思想中,构建“相互非支配”的调节性原则以引导处于冲突和紧张关系中的人们之间的审议。在西方政治哲学史、当代政治理论 (共和主义、民族主义)、比较政治哲学和全球正义等领域著述广泛,近来的发表包括: “A Confucian Reappraisal of Christian Love” (Religions, 2023), “Confucian Role-Ethics with Non-domination” (Ethical Theory and Moral Practice, 2022), “Deliberation with Persuasion: the ‘Political’ in Aristotle’s Politics” (Austral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Global Justice without self-Centrism (Dao, 2021), Modernities in Northeast Asia (Routledge 2023), Machiavelli in Northeast Asia (Routledge 2022), Global Justice in East Asia (Routledge 2020), Leo Strauss in Northeast Asia (Routledge, 2020)。目前担任劳特利奇“东亚语境中的政治理论”系列丛书主编、国际英文期刊《社会和政治哲学》编委。
文章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