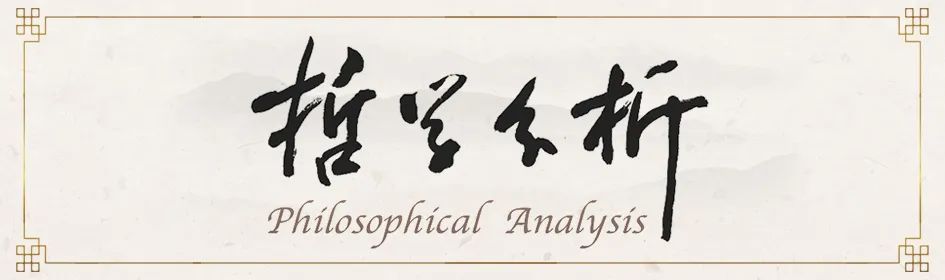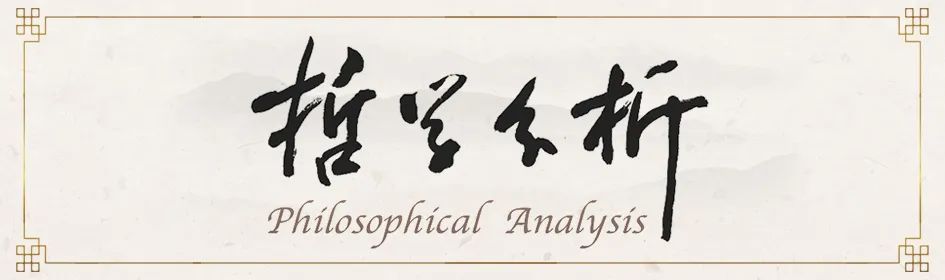
摘要: 理由基本论认为,理由性质是不可还原的基本性质,是规范领域唯一的基本要素。 对理由基本论来说,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理由是什么? 对于这一问题,目前有两种主要观点: 命题主义和事态主义。命题主义认为理由是命题,事态主义认为理由是事态。 然而,命题主义不能满足理由性质的不可还原性限制,事态主义不能满足理由性质的基本性限制。 它们之间的张力可用真理同一论来消解。 同一论认为,作为真理承载者的命题并不是由作为真理制造者的事实使之为真,而是同一于事实。 同一论吸收了当代心灵哲学中的内容外在论思想,避开了元伦理学中的“规范问题”,为实践理由的本体论提供了恰当说明。
关键词: 实践理由; 命题主义; 事态主义; 真理同一论
作者: 王华平,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
一、理由基本论
二、命题主义
三、事态主义
四、同一论
五、结语
正如斯坎伦(Thomas Scanlon)在他最近的一本书中指出,理由已经成为当代元伦理学关注的焦点。 这表现在: 一方面,尽管以麦基(John Mackie)为代表的关于道德话语的解释问题的争论今天仍在继续,但热点已转向如何用理由来说明规范性与实践推理; 另一方面,尽管内格尔(Thomas Nagel)所提出的驱动问题今天仍有零星讨论,但焦点已经从原来的心理基础问题转变成理由问题,即一个人何以会有理由去做道德和慎思所要求的事。 这两方面的转变很快就汇聚成理由基本论(reasons fundamentalism)这一新思潮。理由基本论是这样一个主张: 理由是规范领域的唯一基本要素,诸如善、应该之类的其他规范性概念可以用理由来分析。 假如理由基本论是对的,那么,如何理解理由便是最为要紧的问题。 在这一点上,理由基本论者出现了严重分歧。 一些人认为,一样东西成为理由这一事实(或者说,是理由这一性质),可用非规范的自然事实来解释。 此观点通常被称为自然主义。 另一些人则认为,理由性质是不可还原的基本性质。 此观点又被称为非自然主义。 斯坎伦将非自然主义的理由基本论称为“理由基本论”。 这里,我将在斯坎伦的意义上使用“理由基本论”一词。
对理由基本论来说,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是,理由是什么? 任何回答,要称得上是恰当的,就必须满足理由性质的基本性和不可还原性的双重限制。 关于理由本体论,目前有两种主要观点: 命题主义(propositionalism)和事态主义(statism)。命题主义认为理由是命题,事态主义认为理由是事态。 我将表明,这两种观点都是有问题的。 命题主义的问题是不能满足理由性质的不可还原性限制,事态主义的问题是不能满足理由性质的基本性限制。 在此基础上,我将进一步论证,真理同一论(identity theory of truth)能避开命题主义和事态主义的问题,可同时满足不可还原性限制和基本性限制。 真理同一论认为命题同一于事实,它既是适切的真理理论,也是适切的理由理论。
应当清楚,理由基本论所说的理由指的是实践理由中的规范理由(normative reasons)。 实践理由指的是行动的理由。 与此相对的是理论理由,即支持信念或思想的理由。 通常而言,一个人做出某个行动,会有一些他据以行动的考虑事项。 比如,提交会议论文的截止日期快到了,于是我抓紧时间写文章。 这种情况下,提交会议论文的截止日期快到了就是我据以行动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我们称其为驱动理由(motivating reasons)。 但是,一个人依据某个理由做出某事,并不意味着他就有好的理由去做那事。 我为了能及时提交会议论文而赶文章,但如果我对相关问题并未想清楚,这种情况下,驱动我赶文章的理由就不是个好理由。当我们说一个人有好理由去做某事时,我们说的是,存在一些考虑事项支持(favor)他去做那事。 这样的理由,我们称其为规范理由。
一些人认为,驱动理由和规范理由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理由。 其中较为著名的是,史密斯(Michael Smith)主张,驱动理由是心理状态,规范理由是事实。 现在的主流观点是,驱动理由和规范理由是理由的两种使用方式,而非本体论上不同类型的理由。 当我们谈论的是行动者为什么会做出某个行动时,我们谈论的是驱动问题。 当我们谈论的是行动者是否有好的理由采取某个行动时,我们谈论的是规范理由。 有时,一个人可能出于无知或失误而将一个不好的理由当作好的理由而做出某个行动。 这时,他有驱动理由而没有规范理由。 在另一些情形中,行动者有好理由做某事,但他并没有考虑到那一点。 这时,他有规范理由而没有驱动理由。 假如行动者确实依据好理由做了某件事,这个时候,他的驱动理由就是规范理由。 所以,驱动理由也可以起到规范理由的作用。 反过来,规范理由可以起到驱动理由的作用。 丹西(Jonathan Dancy)称前一点为“规范性限制条件”,后一点为“解释性限制条件”。 丹西认为,上述两个条件合起来可表明,驱动理由和规范理由属于本体论上相同类型的东西。 称此论断为“理由的统一性论题”。 当然,理由的统一性论题是有争议的。 不过,尽管接下来的讨论会涉及这一论题,但并不依赖于它。
理由概念的重要性就在于,诸如好、价值和道德上的对与错之类的规范性概念被认为可以用它来理解。 在此意义上,理由是基本的。 显然,这里所说的理由只能是规范理由,因为驱动理由所使用的语境是解释性的,而不是规范性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规范理由呢? 说某个考虑事项是规范理由,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根据斯坎伦,说某个考虑事项是规范理由就是说它支持某个行动,或者说,它与某个行动处于理由关系中。 斯坎伦认为,具有理由关系是基本事实,无法用其他事实来解释。 即便如此,我们也仍然可以问: 理由关系涉及哪些要素? 斯坎伦的回答是,理由关系是个四位关系,可以用R(p,x,c,a)来表示,其中,p是事实,x是行动者,c是一组条件,a是行动或态度,比如沏茶(行动)、相信某个命题是真的(态度)。 在这四个要素中,x和a是清楚的,p和c则需要澄清。
条件c是理由关系成立的具体情境。 比如,在身边有伞或我不想被淋湿的情况下,下雨才是我打伞的理由。 情境c有可能涉及行动者x的制度身份,例如是某个委员会的成员,凭借这个身份他才能合法地去做a,例如参加答辩。 考虑事项p是事实,或者说,真理(truth)。 如果它只是一个错误的思想,那么它就构不成一个好理由。 假设我出差回来,发现家中的波士顿蕨因缺水而叶尖变黄,那么波士顿蕨缺水这一事实就是我浇水的理由。 假如波士顿蕨并不缺水,而是因为发病而叶尖变黄,那我就没有理由为它浇水。 在这个例子中,事实p是波士顿蕨因缺水而叶尖变黄,情境c是我出差回来,行动a是浇水。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由这些要素组成的关系R(p,c,a)却不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不能还原成自然事实。 理由性质相对于自然界的不可还原性与相对于规范性质的基本性,这两点合起来便是斯坎伦所说的理由基本论。 斯坎伦认为,他的理由基本论是个适切理由。 这是因为,“规范性陈述的本质要素并不是一个指向实体的词项,而是一种关系,即关系R(p,c,a)”,所以,非还原的规范性事实不会带来反常,因而理由基本论并无严重的形而上学上负担。
斯坎伦对理由关系的描述得到了理由基本论者的广泛认同。 丹西所做的一个非实质性修改是将R(p,x,c,a)精简为R(p,x,a)。 丹西认为: “关系成立的条件根本就不是那个关系的一部分。 ”条件的限制性只不过表明,什么支持什么是因情境而异的。 但丹西并不反对R图式,他所做的修改恰恰是以R图式为基础的。 尽管理由基本论者大都赞同用R图式来刻画理由关系,但他们对R图式中事实p的理解出现了严重分歧。 斯坎伦认为,事实p是“真思想”,是“关于世界的命题p”。 这意味着,规范理由就是真命题。 称此观点为命题主义。 丹西认为,事实p不是命题,而是事态(states of affairs)。 这意味着,规范理由是事态。 称此观点为事态主义。由是形成了命题主义与事态主义之争。
命题主义与事态主义并非口舌之争。 根据普兰廷加(Alvin Plantinga)的著名区分,能够为真的东西与能够成为情形(being the case)的东西是本体论上不同的两种东西。 命题能够为真或为假,但不能成为情形。 事态能够成为情形,但不能为真或为假。 事态如果不能成为情形就不成其为事态,但命题即使为假也是命题。 即使每个存在的事态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真命题,事态不也等于真命题。 能够为真的东西是真理承载者(truth-bearer),而使真理承载者为真的东西是真理制造者(truth-maker)。 命题属于真理承载者,事态属于真理制造者。 命题主义认为理由是命题,事态主义认为理由是事态,它们之间的分歧是很明显的。
命题主义的主要支持者斯坎伦将R图式中的事实p解释为真命题,或者说,真理。 但是,斯坎伦却没有给出论证。 也许,他觉得事实就是命题这一点太过显然。 通常,事实与命题都用“S是P”的形式表达。 “雪是白的”,既可以表达事实,也可以表达命题。 在英语中,“It is true that p”与“It is a fact that p”是一个意思,一些人据此认为“事实”一词不过是“真命题”的别名。 但正如莱莫斯(Ramon Lemos)所总结的,“事实”一词至少有四种不同意思: 它可以指真实的实体、出现的事态、事态的出现(obtaining)或不出现、命题。因此,命题主义者需要论证R图式中的事实p是真命题而不是别的意思。
一个自然而然的论证是,理由可为真为假,因此它是命题。 当理由确实支持行动时,我们说它是好理由,有时也称其为真理由。 当我们说某个理由是真理由时,我们强调的是它不是假理由。 假理由分两种: 第一,行动者将误以为真实际却为假的东西当作理由; 第二,行动者以为某个考虑事项支持他的行动,但实际上并不支持。 在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所举的著名例子中,行动者误将一瓶汽油当成是一瓶杜松子酒,因而想喝下它。 这种情形下,行动者的理由因为其信念出错而为假。 假设某种药并不能医治新冠而我相信它可以。 这种情形下,我的理由因为支持关系不成立而为假。 于是就有下面的论证: 理由有真假,命题也有真假,而事态并无真假,所以,理由是命题而不是事态。 但这并不是一个好论证,因为事态主义同样可以谈论真、假理由——当所援引的事态并不存在或并不支持某个行动时,所援引的理由是假理由。
一个经常被提到的论证是,从实践理由在我们决定自己应该如何行动的慎思过程的作用看,它是命题,而不是事态。 在慎思的时候,我们会对事态进行推理(reasoning about)。 例如,我从波士顿蕨发黄的叶尖推出我应该给它浇水。 此时,我慎思的理由是关于事态的。 规范理由可以成为慎思的理由。 规范理由如果称得上实践理由,正如威廉姆斯所指出,就必然有一个“有效的慎思路径”让它影响行动。 对像丹西那样赞同理由的统一性论题的人来说,情况更是如此——规范理由正是通过进入慎思来发挥驱动理由的作用的。 但是,在慎思的时候,我们不只是对某事进行推理,还会用到某样东西进行推理(reasoning with)。 例如在巴巴拉式三段论推理中,我们用全称命题“所有人都会死”和特称命题“苏格拉底是人”进行推理,得出“苏格拉底会死”的结论。 这表明,理由是我们能够用以进行推理的东西,是我们能够在思想中持有和对他人清楚地表述出来的东西。 命题是这样的东西,事态不是,所以,理由是命题而不是事态。 称此论证为实践推理论证。 实践推理论证表明,命题主义比事态主义更为合理。 假如我们接受实践理由的命题主义,给定理论理由已经被认为是命题,那么我们就可以对理论和实践两种推理的前提给出统一解释。
支持命题主义的另一个主要论证是错误情形论证。 这个论证说的是,当行动者将他错误地相信的东西当作行动的理由时(即前文所说的第一种假理由),由于世界中并无相应的事态,所以他行动的理由不可能是事态,而只能是命题,即作为他错误信念的内容的假命题。 因此,驱动理由是命题。 给定理由的统一性论题,我们就可得出结论,规范理由是命题。
错误情形论证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它在排除了事态后就断言命题是理由的最佳候选者。 一些人,例如戴维森和史密斯,认为行动者据以行事的理由(即驱动理由)是心理状态。 这个观点通常被称为心理主义(psychologism)。 然而,心理主义并不是一个好的选项。 设想一位女士因为相信自己经常被跟踪而报了警,她向警察陈述时,多半会说自己发现了被跟踪这一事实而感到安全受到了威胁。 假如她真的会根据自己的相信状态做出某个行动,她多半是去看医生——她怀疑自己得了妄想症。 即使在这样的罕见情形中,行动的理由也很难说是行动者的心理状态,而不是她所意识到的她处于那个状态这一事实。 此外,心理状态与事态一样,是行动者在慎思时可以对之进行推理但不能用于推理的东西。 因此,心理主义与事实主义一样面临来自实践推理的压力。 综合以上两点,可以断言心理主义不足以与命题主义竞争。
其次,错误情形论证用到了理由的统一性论题,而统一性论题是有争议的。 对不赞同此论题的人来说,他们可以承认驱动性理由是命题,并同时认为规范性理由是事实。 但这种观点会导致一个古怪的推论,即规范性理由通过“有效的慎思路径”进入慎思时会发生本体论上的变化——从事态变成命题。 事实上,尽管统一性论题仍有争论,但它也获得了大量认同。 特别是,这场争论的双方,例如丹西、斯坎伦和帕菲特,都赞成统一性论题,因而可以将它看作是一个无害的预设。
最后,错误情形论证默认了行动者在错误情形中有规范理由。 在错误情形中,行动者依据某个考虑事项做出了某事,那个考虑事项构成他据以行事的理由。 这样的理由,如前面所说,是驱动理由。 然而,在错误情形中,行动者的驱动理由并不是好理由——在错误情形中,行动者或者将误以为真实际却为假的东西当作理由,或者误以为某个考虑事项支持他的行动,但实际上并不支持。 这两种情况下,行动者所援引的考虑事项都不支持他的行动。 所以,一个坏理由不仅仅不是一个好理由,而根本就不是理由。 正因如此,很多人,例如丹西、斯托特(Rowland Stout)、阿尔瓦雷茨(Maria Alvarez),认为在错误情形中行动者只是具有“表面上的理由”(apparent reason),实际上并无理由。 显然,这里所说的理由是规范理由。 错误情形论证从错误情形中驱动理由只能是命题推出规范理由是命题,这是无效的。
尽管错误情形论证是无效的,但仍然可将它与理由的统一性论题结合起来向命题主义提供支持。 假如驱动理由如错误情形论证所证明的是命题,给定理由的统一性论题,那么规范理由也是命题。 经过这样的改进,错误情形论证被认为很好地支持了命题主义。 在错误情形论证和实践推理论证的双重保证下,命题主义在这场争论中被当作默认立场。 它的反对者更多地是以它为攻击目标,而不是直接论证与之相竞争的那些观点。
事态主义的支持者丹西对命题主义进行了系统反驳。 反驳的第一步是这样的: “从直觉上看,理由更像是事态而不是命题。 是她病了(her being ill)给了我送她去看医生的理由,这是一个事态,是属于世界中的一部分的东西,它不是命题。 ”可是,有时我们会将像她生病了(that she is ill)这样为真的东西当作理由。丹西认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对“为真的东西”与“成为情形的东西,或是如此这般的东西”作出一致区分。 丹西由是断言: “日常用法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什么帮助。 ”既然如此,我们也就不能仅凭直觉来反驳命题主义。
在反驳的第二步,丹西分析了命题的不同理解方式,指出它们都不足以胜任理由的角色。 第一种理解方式是跟随刘易斯,将命题看作那些在其中表达那个命题的句子为真的可能世界的集合。 第二种理解方式是跟随弗雷格,将命题看作其结构反映断言句的结构的抽象实体。 弗雷格式命题由名称和概念,而非它们所指称的事物和性质组成。 这两种理解方式都将命题看作抽象实体,而不是世界的一部分。 丹西认为,这样的命题“太单薄或太没有实质性”,对理由来说是“类型错误的东西”。 不妨称此反驳为单薄反驳。 单薄反驳的关键点在于,命题是抽象的,但行动的理由不能是抽象的。可是,为什么实践理由不能是抽象的呢? 对此,丹西并未给出进一步说明。 不过,我们可以顺着他的意思补充如下论证:
(1)命题是抽象的;
(2)行动是具体的;
(3)抽象的东西不能影响具体的东西;
(4)规范理由必须能够影响行动;
结论: 规范理由不是命题。
前提(1)是对弗雷格命题和可能世界命题分析的结果。 前提(2)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 前提(3)是否成立依赖于其中的“影响”是什么意思。 如果“影响”意指因果作用,然则前提(3)是对的,但(4)并不成立。 这是因为,非时空中的抽象实体不能与时空中的具体对象产生因果作用。 实际上,理由基本论认为规范理由与行动之间是支持关系而非因果关系。 规范理由对行动的影响只能通过支持关系来实现。 这种影响,正如丹西所指出,是“使之应该”。 也就是说,理由对行动的影响是,它使得它所支持的行动是应该的,或者说,行动是凭借(in virtue of)理由的力量获得应该性(oughtness)的。 “凭借”表达的是形而上学上的奠基(grounding)关系,即一种现象“建立”(built)在另一种现象之上。 奠基关系的关系项可以是抽象的,也可以是具体的,但需要它是“事实”。 以此观之,如果像命题主义那样将作为奠基关系的关系项的“事实”解释为抽象命题,那么前提(3)碰巧是对的(因为被影响的东西也只能是抽象命题)。 问题是,抽象命题是否能为行动奠基,赋予它应该性?
在反驳的第三步,丹西力图说明,抽象命题不能赋予行动应该性。 命题有真假之分: 命题为真的意思是它将世界中的事态表征成正确的样子,为假则表示表征不准确。 所以命题是表征。 那么,表征能成为理由吗? 一些表征,例如照片和地图,它们本身是实物。 但实物不能成为理由。抽象命题不是实物,它是“裸表征”(naked representation),即没有表征物的表征。 像照片之类的表征拥有表征物,即有图案的像纸。 表征物具有非表征性质,凭借非表征性质它将对象表征这样而不是那样。但裸表征没有借以表征的非表征性质,它是透明的,就像没有颜色性质的玻璃一样。 当我们向透明表征寻找行动者的应该性的基础时,我们找到的将是透明表征所指向的东西,即它所表征的世界中的事态。 这表明,理由不是作为透明表征的命题,而是命题所表征的事态。 称此反驳为表征反驳。 面对表征反驳,命题主义者也许会争论说,尽管一般命题不能支持行动,但真命题可以。 可是,承认这一点等于承认起支持作用的不是命题,而是它的真。 由于使得一个命题为真的是事态,所以这等于承认起支持作用的是事态,从而承认事态主义是真的。
单薄反驳和表征反驳旨在表明,命题主义是有问题的。 命题的本体论地位决定了它不适合充当实践理由。 假如可充当理由的候选者只能在命题与事态之间选择,那么,理由是事态而不是命题。 以此观之,单薄反驳和表征反驳不仅仅是反驳了命题主义,而且还支持了事态主义。
现在我们清楚了命题主义与事态主义之争。 如何化解这场争议呢? 一种方案是坚持命题主义,但这需要消解单薄反驳和表征反驳。 先看单薄反驳。单薄反驳的补充论证是有问题的,问题就在于前提(2)。前提(2)断言行动是具体的,但规范理由所支持的行动并非都是具体的,因为有些行动根本就没有做出来。 比如,一个新冠患者不知道他前面的一种药可以治疗新冠而没有理会它。 即使如此,他仍然有理由吃下那种药。 这种情况下,吃下那种药并非具体的一个行动,而是抽象的一类行动。 当行动者依据规范理由做出某个行动时,他所做的那个行动是具体的,那个行动当然受到规范性理由的支持。 不过,这种支持是派生的——它源于规范理由对抽象的一类行动的支持。 具体行动由于在情境c中例示了那类行动,因而继承了规范理由对那类行动的支持关系。如此看来,斯坎伦用R(p,x,c,a)来刻画理由关系是对的。 这是因为,尽管情境c不是纯粹的规范理由关系的一部分,不过对驱动理由来说,它确实是理由关系的一部分。
尽管单薄反驳是可消解的,但表征反驳却不然。 理由要为行动的应该性奠基,它就必须承担起奠基的责任。 但是,给定命题的透明性,它会将奠基的责任推卸给它所表征的事态。 这意味着,命题主义版本的R(p,x,c,a)不是基本的——它可用另外的东西(即事态)来解释。 因此,命题主义不能满足理由性质的不可还原性限制,不能与理由基本论相兼容。 对自然主义来说,表征反驳也许没那么有力。 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追问,给定命题的透明性,命题凭借什么成为行动的理由呢? 这个问题对自然主义语境下的命题主义仍然构成压力。
表征反驳似乎将胜负的天平拨向了事态主义一边。但要坚持事态主义,就要驳倒实践推理论证和错误情形论证。 对于实践推理论证,丹西的处理方法是区分推断(reasoning)和推理(inference)。 推理,就像我们通常理解的那样,有前提和结论。 推断则既没有前提,也没有结论。 在实践推断中,一个人从所考虑的事项推出那些考虑事项所支持的行动,这并不是从前提到结论的推理过程。 在作出这样的区别后,丹西指出,实践推理论证是以实践推理为基础的,并不适用于实践推断。 然而,直觉告诉我们,慎思所涉及的的确是推理,而非丹西所说的推断。 因此,实践推理论证是有效的。 丹西对错误情形论证的处理也不尽人意。 仅仅说错误情形中行动者没有理由是不够的,这驳不倒改进后的实践推理论证。
更为重要的是,事态主义有着比上述两个论证所指出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是,它不能满足理由性质的基本性限制。 根据理由基本论,理由性质是最基本的规范性质,其他规范性质可用它来解释。 这意味着,理由所是的东西的确可以赋予行动应该性,为行动“制造”规范性质。 事态主义认为命题不行,事态可以。 但是,如果理由仅仅是世界中的事态,它又是如何成为行动者的理由的呢? 或者用科斯嘉的话来说,理由是如何“控制”(get a grip on)行动者的呢? 科斯嘉称此问题为“规范问题”。
规范问题实质上是理由关系是否成立的问题。 理由基本论试图用理由关系来解释所有规范性性质,这要求理由关系本身是规范的。 可是,如果R图式中的p仅仅是世界中的事态,它又怎么能够与R图式中的x、c、a一起激发出不可还原的理由关系呢? 这个问题是著名的“是”与“应该”问题的当代版本。休谟曾指出,描述层面的“是”与规范层面的“应该”之间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安斯康姆(Elizabeth Anscombe)用一个例子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一个杂货店老板送了一夸特(28磅)土豆到我家并递给我一张账单,从这些事实推不出我欠他买土豆的钱。 这是因为,杂货店老板送土豆到我家并不等于他卖给我土豆——他有可能叫人马上将它拿走。 即使加上他不拿走这一限制条件也不行,因为他有可能出于忽发奇想而将土豆送到我家。总之,你无法给出一个完整的描述将杂货店老板送土豆到我家限制为他卖土豆给我。 我当然能够知道杂货店老板卖了土豆给我。 假如你问我如何知道这一点,我会回答说: “我向杂货店老板下了订单,然后他将土豆送到我家。 ”在这样的“程序正常”的语境中,我将杂货店老板送土豆到我家“描述”为他卖土豆给我。 相比于卖土豆给我,送土豆到我家是“原始事实”(brute fact)。 从杂货店老板送土豆到我家这个原始事实看,我没有理由做出支付杂货店老板一笔货款这一行动。 但是,一旦我将杂货店老板送土豆到我家这一原始事实描述为他送货给我,我就会明白自己欠杂货店老板货款,就会有理由做出支付杂货店老板一笔货款这一行动。
与安斯康姆相呼应,科斯嘉富有启发地作出了“作为对事实的反应的行动”与“作为对事实的描述的反应的行动”的区分。 一只母狮可能会对事实作出反应,例如将它的幼崽带来安全的地方,但这并不是将对那个事实的描述作为理由而做出行动。 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能对事实的描述作出反应,例如一个意大利的那不勒斯人将同伴往外刮下巴的动作描述成同伴讨厌他,从而愤怒地离开他的同伴。
清楚了描述之于理由关系的不可或缺作用也就清楚了事态主义的问题所在。 问题就在于,对理由关系来说,独立于描述的事态显得过于原始。 有资格成为理由的东西必定是描述层面的东西,而描述层面的东西属于真理承载者。 这等于将理由往真理承载者那边推。 另一方面,作为真理承载者的命题又会因为自身的透明性而将责任转嫁给属于真理制造者的事态。 这等于将理由往真理制造者那边推。 如果真承载者与真制造者始终只是由诸如符合之类的关系联系起来的形而上学上不同种类的东西,那么,实践理由将变得不可能。 反过来,如果实践理由是可能的,那么就必须承认真理承载者与真理制造者有合二为一的可能。 历史上,观念论持此观点。 观念论认为,观念是世界的基本成分,也是真之所在。 但观念论已为我们这个时代所抛弃。 在今天,真理同一论持此观点。真理同一论认为,作为真理承载者的命题并不是由作为真理制造者的事实使之为真,而是同一于事实。 既然作为真理承载者的命题同一于作为真理制造者的事实,那么,由于真理承载者与真理制造者的分离而产生的问题,包括命题主义的透明性问题和事态主义的原始事实问题,也就是烟消云散了。
实际上,丹西在批评他所谓的“以内容为基础的策略”(content-based strategy)时已经暗示了真理同一论的解决方案。 根据“以内容为基础的策略”,驱动理由是具有如此那般内容的心理状态,规范理由是心理状态的内容。 丹西对“以内容为基础的策略”的批评是,它让“使得它可行的心灵哲学变得非常古怪”。 这是因为,在心灵哲学中,信念的内容普遍被认为是命题。 由于规范理由已经被认定为是事态,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个推论: 命题就是事态。 丹西认为这个推论会让心灵哲学变得“非常古怪”。 但实际上,至少在普特南(Hilary Putnam)之后,这个推论已不再古怪。 普特南之后,心理内容的外在论已然成为心灵哲学的主流。 根据内容外在论,有一些心理状态的内容是由外部环境中的要素构成的。 更强版本的外在论认为,有一些心理状态以罗素式命题为内容。 罗素式命题由物体及其性质本身组成,因此,罗素式命题与事实是同一的。 强外在论承诺了罗素命题就等于承诺了真理同一论。 强外在论不但是当代心灵哲学中的一个有竞争力的观点,而且在一些人看来,例如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它根本就是“自明之理”。 作为自明之理,当一个人思考雪是白的时,他所思考的是雪是白的这一世界中的事实。 因此,当我们正确地思考时,情形如此既是思想的内容,也是世界的一个方面,两者之间没有“本体论的间隙”。
当然,我们的思想有可能出错。 当我们的思想出错时,我们以为自己把握了世界的一个方面,实际上却没有。 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进行了错误表征,它的内容是一个假命题。 假命题不可能是罗素式命题,但可以是弗雷格式命题,也可以是可能世界命题。 我所主张的同一论认为,规范理由是罗素式命题,基于错误信念的假理由是弗雷格式命题。 弗雷格式命题可用于推理,不存在实践推理论证所说的问题。 这样一种同一论当然是一种形式的析取论。 不过,这种析取论不会产生理由进入慎思时发生本体论上的变化的问题,因为析取支是根据理由的本体论而非它的功能来划分的。并且,这种析取论可以避开改进后的错误情形论证,因为错误情形中理由的统一性论题只是在合取层面上才有效,即驱动理由和规范理由同属命题; 在析取层面上,它并不成立,因此,不能从错误情形中驱动理由是弗雷格式命题推出规范理由也是弗雷格式命题。
也许有人会反对说,我所主张的同一论只不过是改变了事实的定义。 事实一般指出现的事态或事态的出现,而我将它说成是命题,这不过是语词之别。 但情况并非如此,当我说事实与命题同一时,我的意思不是将事实重新定义为命题,而是说作为真理制造者的世界中的事实(也即事态主义者所说的事实)同一于作为真理承载者的命题(也即命题主义者所说的命题)。 一些人,例如恩格尔(Pascal Engel),认为这样的同一论主张会招致形而上学上的反常。 按照恩格尔的说法,世界中的事实属于弗雷格意义上的指称领域的居住者,而抽象的命题属于含义领域的居住者,将它们混为一谈不免会陷入唯心论。 但正如麦克道尔所指出的,这样的指责误解了弗雷格的含义与指称概念。 弗雷格所说的含义就是思想,而思想是一个人所想(或所说)的东西,即“可思物”(thinkables)。 “可思物”不同于对“可思物”的“思考”(thinking),它是可以成为情形的东西,是世界的一部分。 将思想同一于思考会陷入唯心论,但同一于可思物不会。
按照上面的理解,命题与事实都是含义领域的居住者。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谈论指称。同一论当然承认存在指称领域,并且认为可以将“世界”的概念运用于它。 不过,这样的世界并不是由可成为情形的事物构成的世界,至少在弗雷格所使用的可成为情形的事物的概念上是如此。 属于指称领域的世界与属于含义领域的世界当然有联系——前者支撑着后者。 如果你仍然觉得难以理解,那么不妨将前者类比成颜色事实世界,将后者类比成物理物体世界。 颜色不是物理物体自身的性质,物理物体世界中没有颜色事实。 但是,物理物体被表征后就产生了颜色,就有了物理事实,比如说雪是白的,草是绿的。 这些事实尽管依赖于表征,却是很好理解的普通事实。 同一论所说的同一于命题的事实就像是颜色事实,它们是思想可达的世界中的普通事实。如此看来,同一论所说的事实一点儿也不神秘。
现在,我们为实践理由找到了合适的本体论: 同一于命题的事实。 如果理由只是原始事实,那么我们就需要另外的事实来解释原始事实为何能成为行动者的理由,就像我们需要另外的事实来解释为什么杂货店老板送土豆到我家我就要支付他货款一样,而这正如安斯康姆所指出,是一个无法完成的任务。 可是,如果我能看出杂货店老板是卖土豆给我,那么我自然就会支付他货款。 理由,正如塞拉斯(Wilfrid Sellars)所说,是“理由空间”(space of reasons)中的居住者。 自然空间的一个事项,只有在将其纳入理由空间后才能成为理由。 命题主义和事态主义都没有领略到这一要旨,它们要么忽视了自然空间,要么轻视了理由空间。 同一论克服了它们的问题,为实践理由的本体论提供了恰当说明。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中后期元伦理学研究”(项目编号: 19ZDA036)阶段性成果。
一、本刊对所有来稿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未委托任何机构或个人代为组稿。
二、本刊严禁一稿多投,如因作者一稿多投给本刊造成损失的,本刊保留追究作者法律责任的权利。
三、作者投稿请登录《哲学分析》官方网站 http://zxfx.cbpt.cnki.net。
四、本刊联系方式为021-64280039。
《哲学分析》编辑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