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研讨会会议纪要
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研讨会会议
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
研讨会会议纪要
2022年11月19日至20日,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研讨会顺利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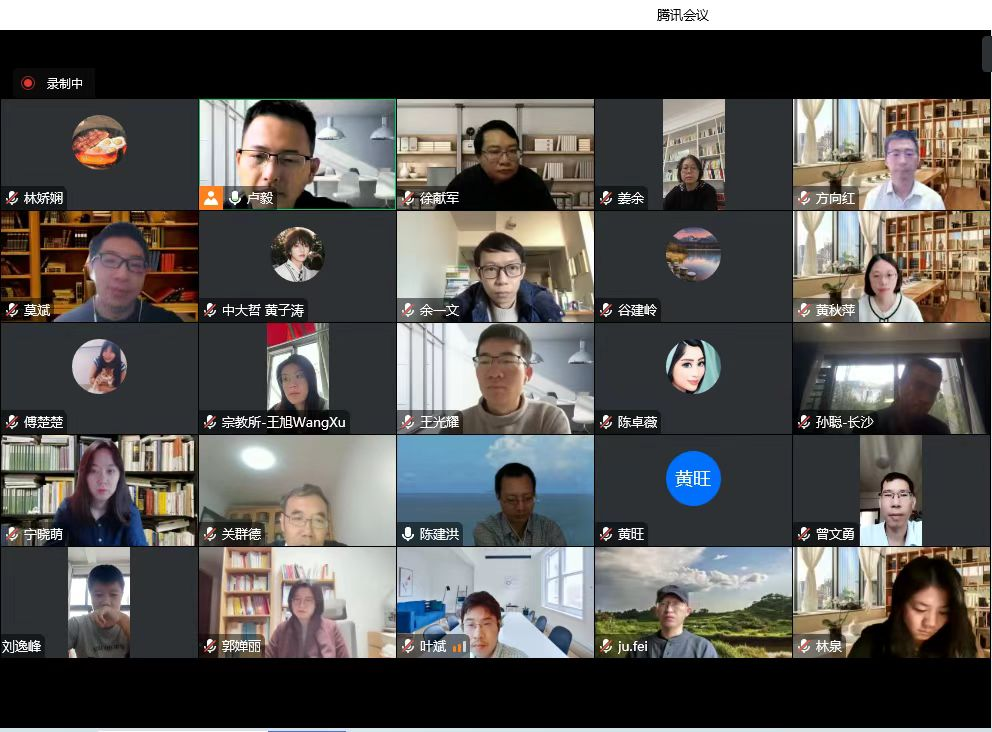
11月19日上午,我系系主任陈建洪教授为本次研讨会致开幕辞。
第一场研讨
第一场研讨由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的莫斌副编审主持。
来自中山大学的方向红教授做了第一场报告,题目是“困在时间中——一个现象学的描述和咨商方案”。

来自同济大学的徐献军教授做了第二场报告,题目是“无意识和阿赖耶识”。

在讨论环节,王亚娟老师针对方老师报告中的空间线之困提出问题。
居飞老师则从如何看待记忆混乱这个角度提出问题。
第二场研讨
第二场研讨由同济大学的居飞副教授主持。
来自浙江大学的郭婵丽博士做了第三场报告,题目是“情感、身体及‘肉’——亨利与弗洛伊德学说中的身体问题”。

来自厦门大学的黄秋萍博士做了第四场报告,题目是“论精神分析伦理学中的善与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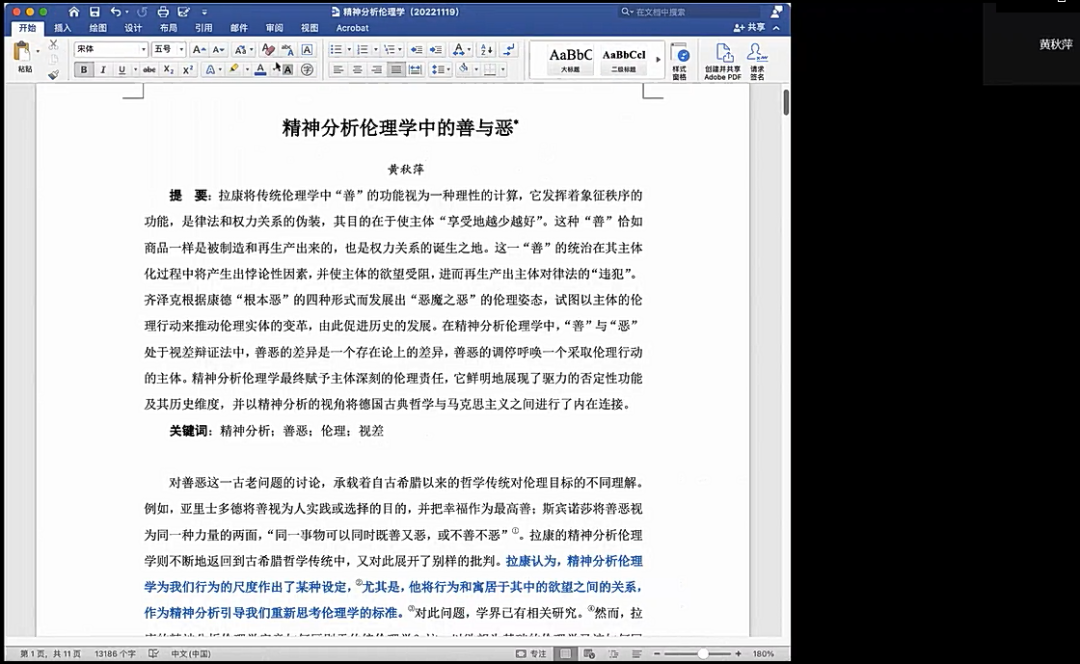
在讨论环节,居飞老师针对文本的翻译提出问题,他更倾向于将“Trieb”翻译为“冲动”,这样能更好地体现弗洛伊德这个概念的哲学起源,更关键的还在于弗洛伊德将“冲动”定义在身体和精神之间,如果译为“力”(欲力或驱力),会太过偏向机械论,过于关注其生物起源而忽略其精神的一面。
卢毅老师和黄秋萍老师针对拉康关于律法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黄老师认为“揽责”有拯救的意味,在拉康的语境下是主体被赋予一个神圣的使命,对“大他者”的空洞和匮乏进行揽责,而在马克思哲学中,则是无产阶级被赋予了这一角色和使命。
王光耀老师针对亨利在哲学史上的定位提出一个问题,即亨利是否能纳入到斯宾诺莎的内在主义当中?
第三场研讨
第三场研讨由浙江大学的马迎辉研究员主持。
来自南方医科大学的黄旺副教授做了第五场报告,题目是“生死欲力‘之间’的逻辑——德里达《生死》研讨班与理解解构哲学的一条线索”。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曾文勇做了第六场报告,题目是“欲望的结构与解构——拉康欲望理论的阐释与辨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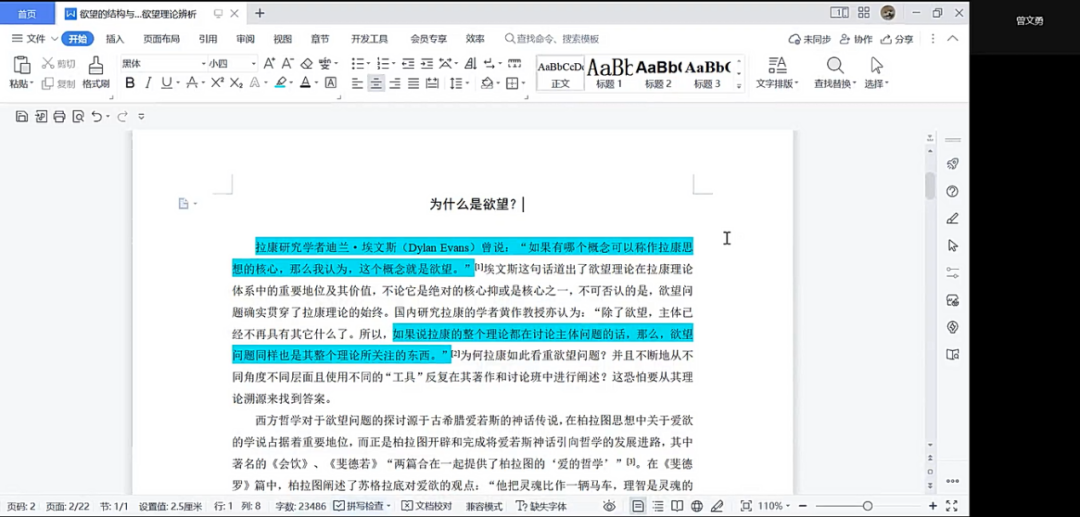
在讨论环节,卢毅老师认为黄旺老师的报告揭示了弗洛伊德和德里达的关系(精神分析和解构哲学的关系)这样一个很重要但常被国内学界忽视的问题。
马迎辉老师向黄旺老师的报告提出一个困惑,即德里达的解构如果是以活的在场为基础而非讨论在场本身如何建构起来的话,那么德里达的“死”最多只是“睡眠”,而非真正的死亡。
卢毅老师同曾文勇博士生就拉康欲望理论的社会-政治哲学效应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第四场研讨
当日下午,本次研讨会的第四场研讨由中山大学的朱刚教授主持。
来自南开大学的林建武副教授做了下午的第一场报告,题目是“作为‘神经错乱者’的‘人质’:论列维纳斯与弗洛伊德的 ‘创伤’概念”。

来自苏州大学的王光耀老师做了下午第二场报告,题目是“快乐与善——列维纳斯及其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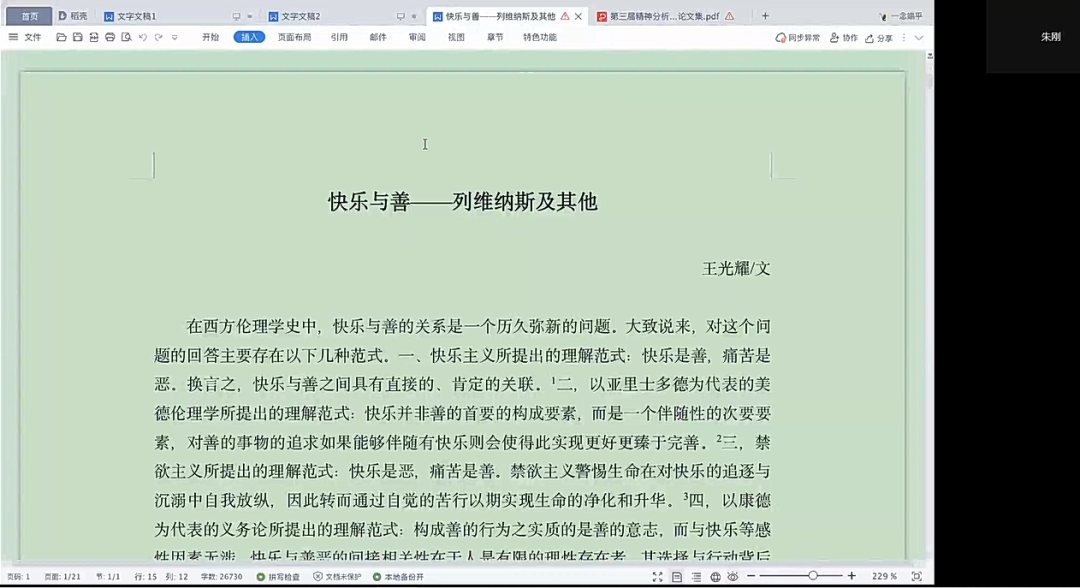
在讨论环节,主持人朱刚老师就“精神错乱”的翻译问题以及对感性享受的存在论层面与存在者层面的区分问题分别与两位报告人进行了探讨。
第五场研讨
第五场研讨由来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傅楚楚主持。
来自埃塞克斯大学的王晨阳老师做了下午的第三场报告,题目是“象征和主体间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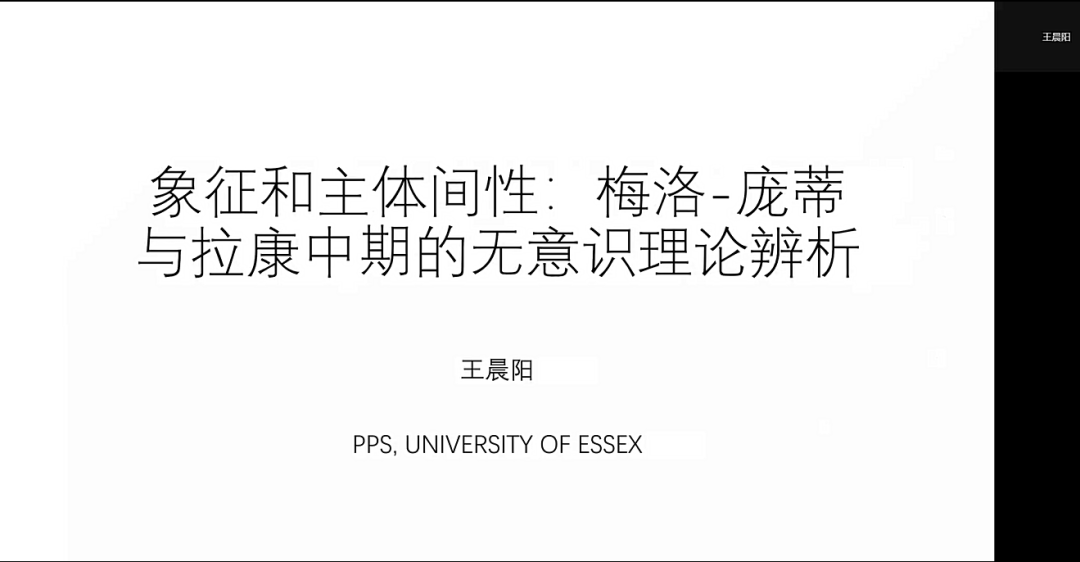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孙聪做了下午的第四场报告,题目是“从内主体性到主体间性——梅洛-庞蒂的‘无意识’观初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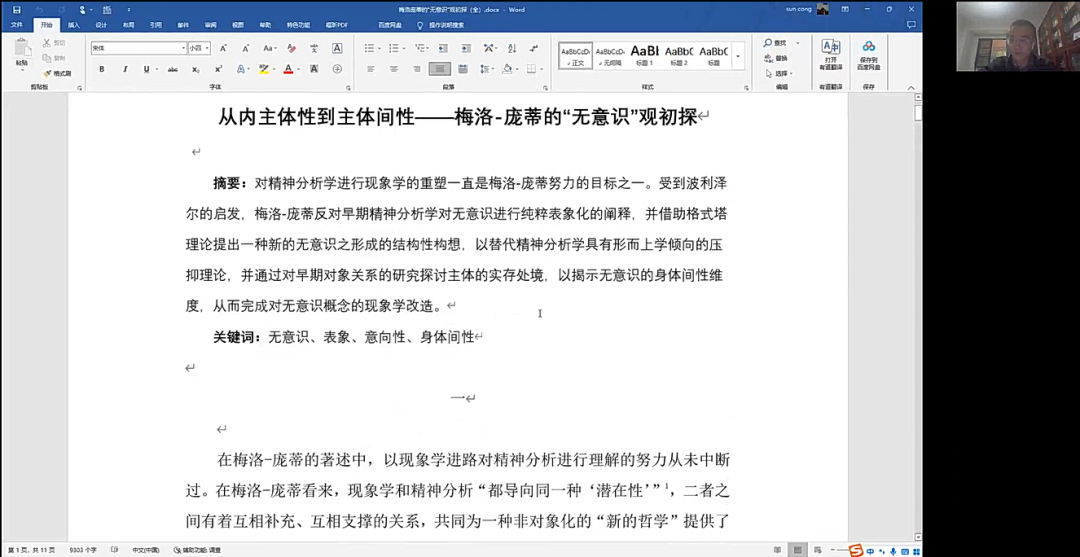
在讨论环节,余一文向孙聪提出了问题。
接着,卢毅老师认为:
第六场研讨
第六场研讨由四川大学的谷建岭老师主持。
来自广西民族大学的刘逸峰博士做了下午第五场报告,题目是“‘母亲’的意义与主体之孤独——在弗洛伊德与胡塞尔之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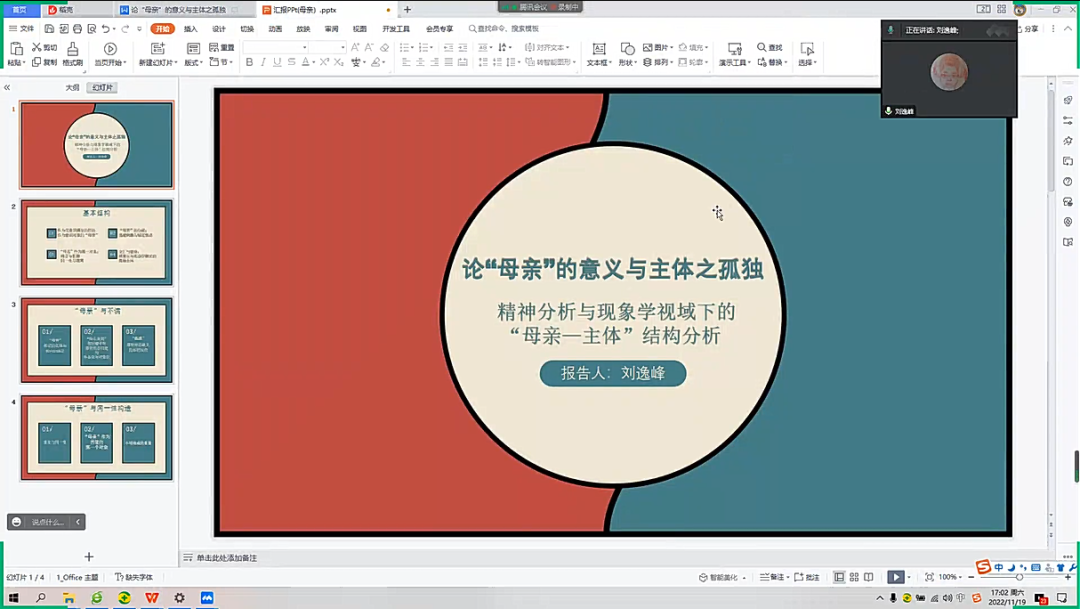
来自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博士生陶佳意做了下午第六场报告,题目是“重复与精神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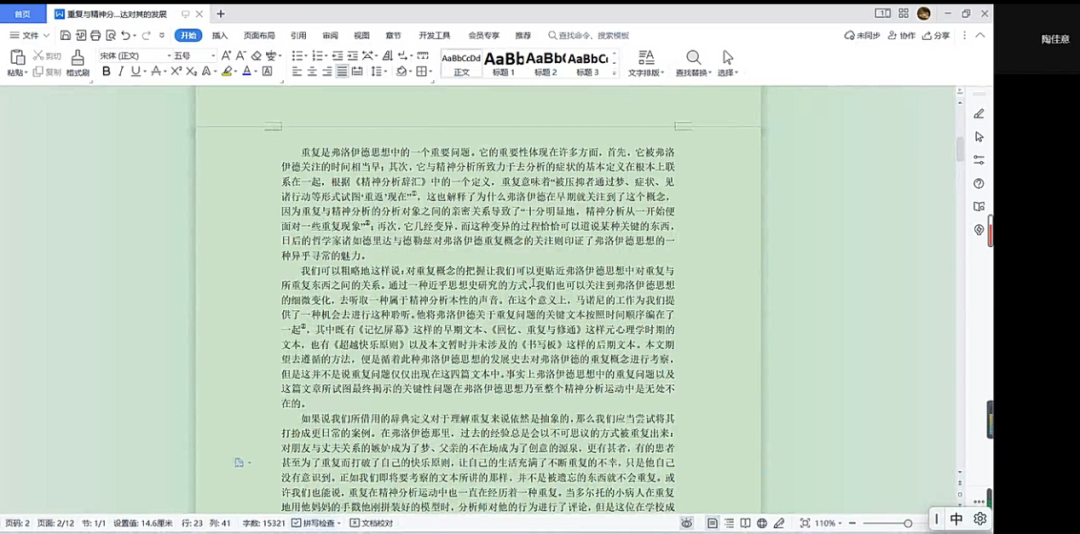
第七场研讨
11月20日上午,第七场研讨由商务印书馆的关群德编审主持。
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宁晓萌副教授做了第一场报告,题目是“一种特殊的交互主体关系研究——梅洛-庞蒂论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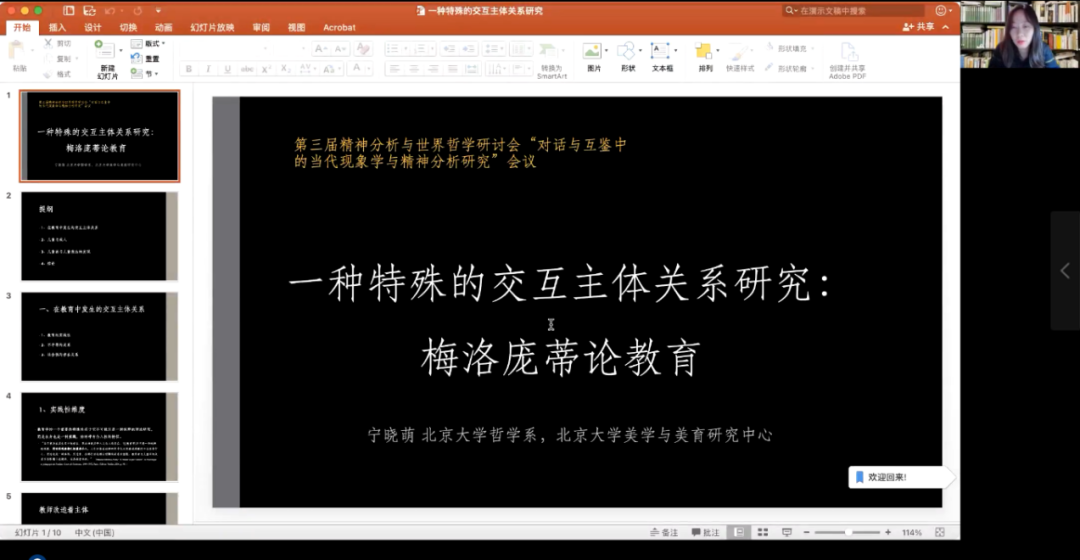
来自南开大学的王亚娟副教授做了第二场报告,报告题目为“肉身的谱系——梅洛-庞蒂现象学与弗洛伊德主义的交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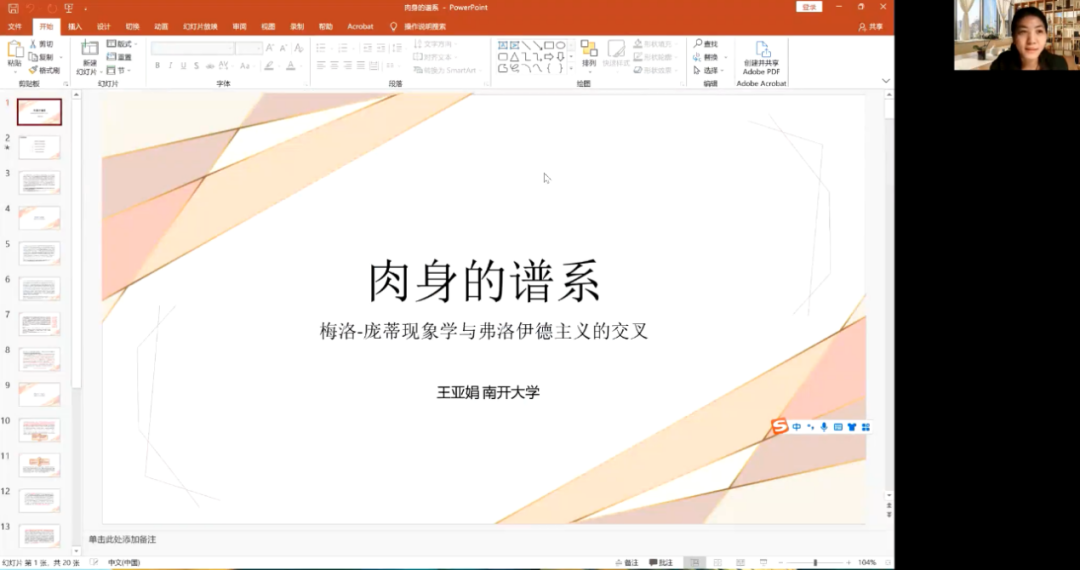
在讨论环节,孙聪向宁晓萌老师提出了问题。
对于这一问题,宁晓萌老师认为梅洛-庞蒂在这一问题上是比较中立的,他更强调的是一种互相为了彼此的存在,而不是单方面的为我或为他的存在,他始终关注的是一种相互关系,因此这个他人是自我与他人的张力之中的一个他人因素。
接着,卢毅老师向王亚娟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希望王老师能够澄清欲望谱系的内涵。
王亚娟老师指出,报告题目中“肉身的谱系”是从肉身的缘起、运作机制及其内涵来谈论谱系学。

第八场研讨
第八场研讨由东南大学的姜余老师主持。
我系的卢毅副教授做了第三场报告,题目是“弗洛伊德学说中的无意识意向性与心理决定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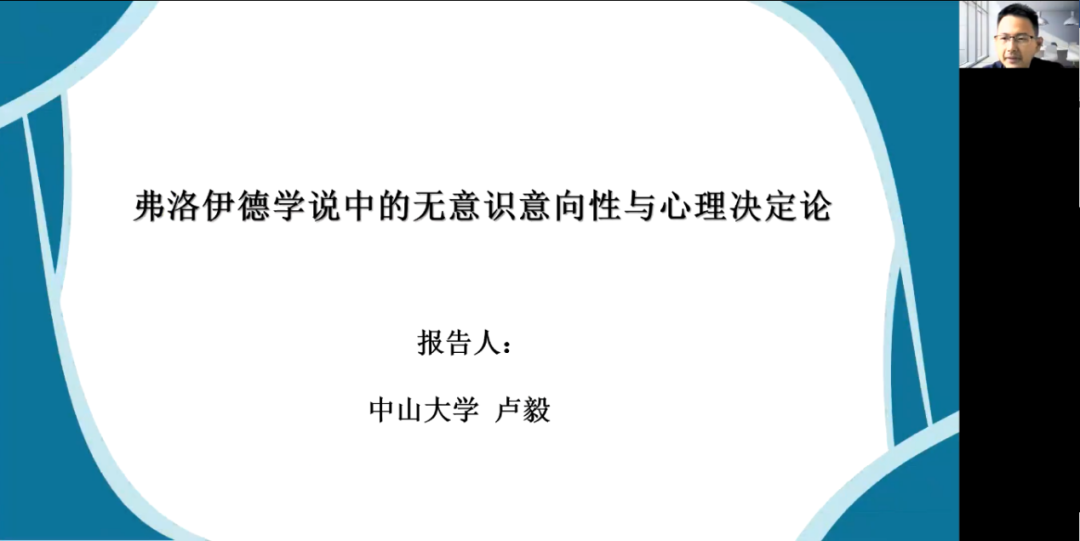
来自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崔丽俐做了第四场报告,题目是“列维纳斯的伦理时间:

在讨论环节,姜余老师向崔丽俐提出了两个问题。
对于第一个问题,崔丽俐指出列维纳斯实际上认同胡塞尔和海德格尔对于时间性的思考,但不同之处在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讨论的更多是个体或个体自我的时间性,列维纳斯要做的就是跳出这个个体自我去追问时间性的条件,把时间性的问题带回到父子关系和母子关系。
接着,余一文向卢毅老师提出了问题,认为卢毅老师把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意图作为一种区别于现象学和形而上学的另外一种意图来解读的方式是可行的,但是是否也有另外一种矛盾的解读方式,即把把无意识概念还原为现象学意义上的意识维度?
卢毅老师认为这一问题是精神分析和现象学争论不休的一个问题。

第九场研讨
第九场研讨由中山大学的卢毅副教授主持。
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旭博士做了第五场报告,报告题目为“福克斯以身体为核心的现象学人论——兼论其对脑神经科学的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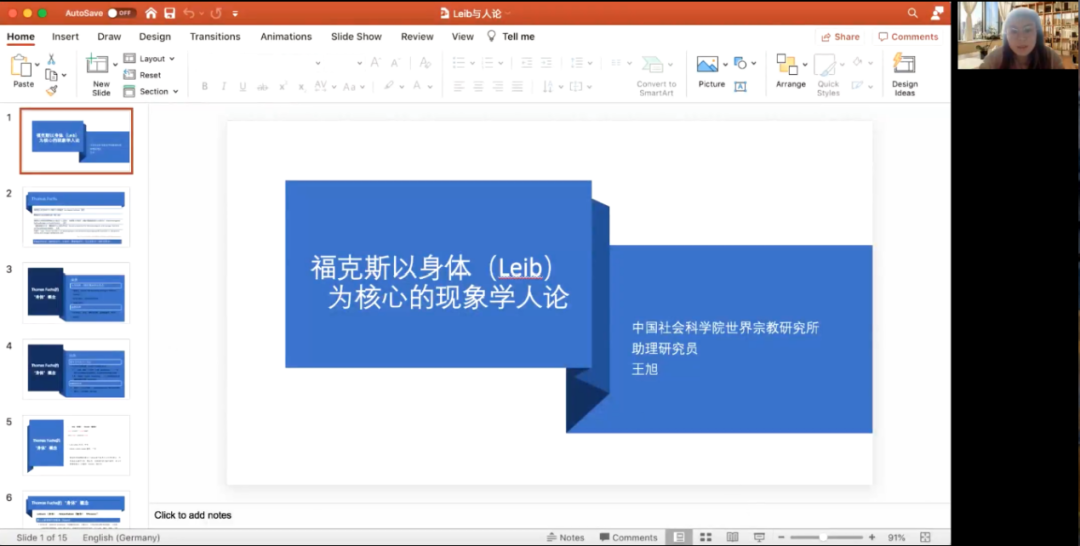
来自华南师范大学的博士生余一文做了第六场报告,题目是“同感现象(Einfühlung)和无意识的假设——利普斯、弗洛伊德和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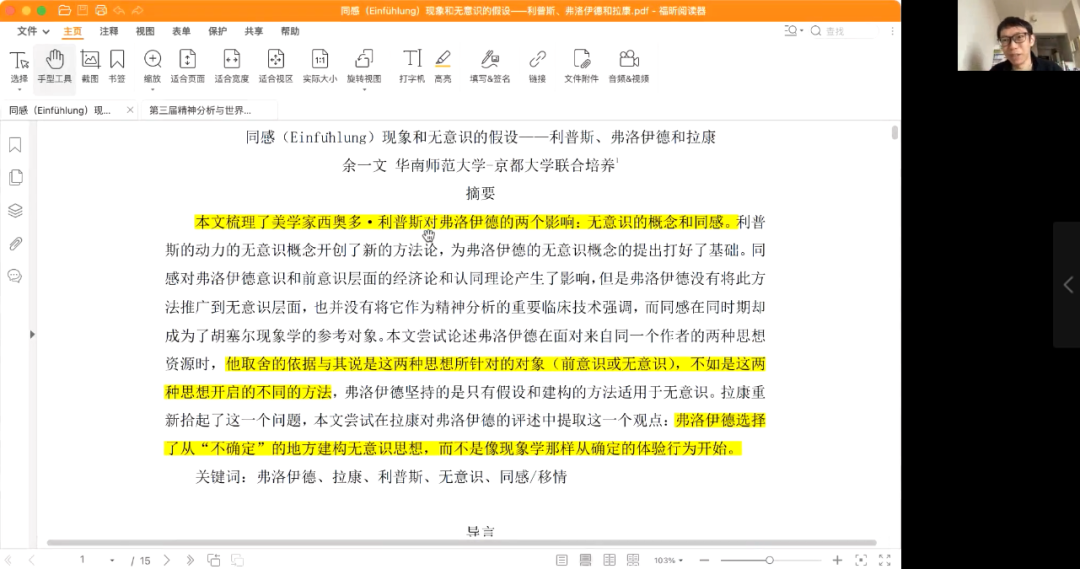
在讨论环节,王亚娟老师针对福克斯关于“自我极”的态度向王旭老师提出了问题。
接着,卢毅老师对余一文的报告提出了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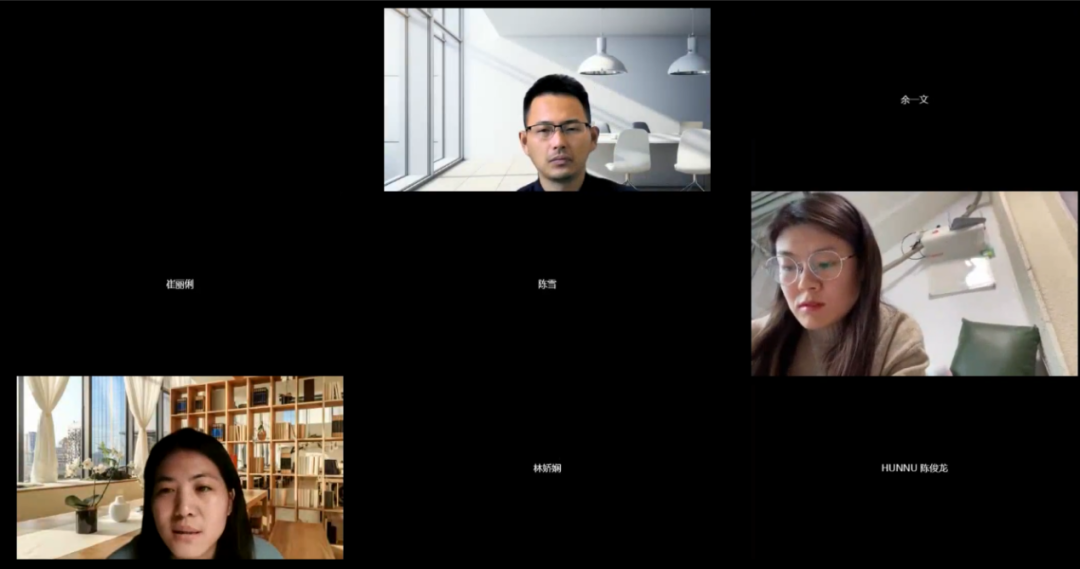
随着第九场研讨的结束,第三届精神分析与世界哲学研讨会也落下了帷幕。
来源|哲珠新媒体
文案|陈佳华 王琳华 王雪曼 王睿 陈欣宇 林娇娴
编辑|汪俊豪
初审|黄丹萍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