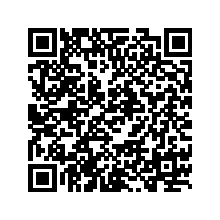学术资讯|我系蔡祥元教授发表文章:自然机制还是意义机制——现象学与自然主义在他心感知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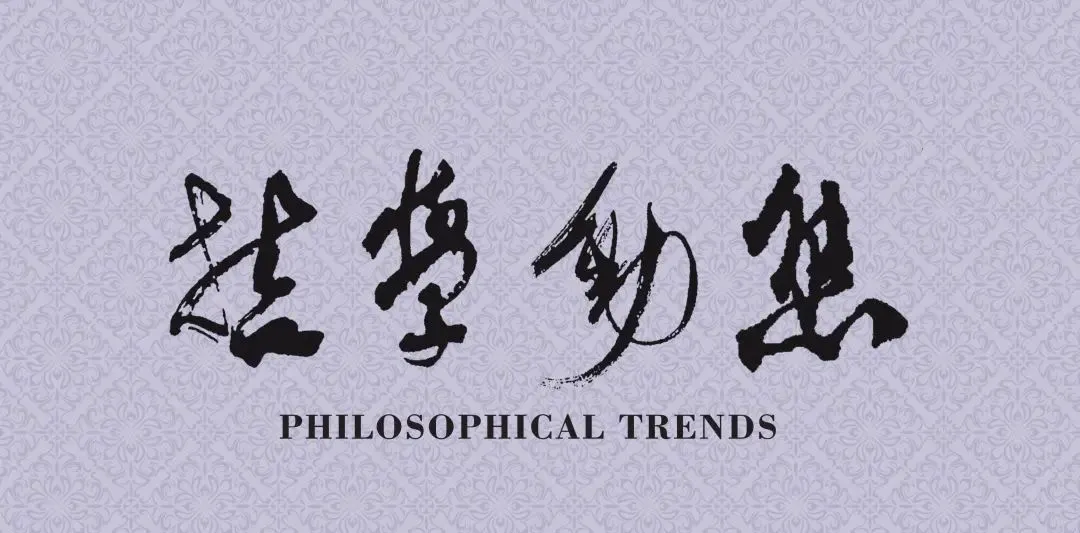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办
自然机制还是意义机制
——现象学与自然主义在他心感知问题上的共识与分歧
蔡祥元
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
本文来自《哲学动态》2025年第6期
“当代西方哲学前沿”栏目
[摘要]在如何感知他心的问题上,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他心直接感知理论有一些基本共识。它们都反对通过推论的方式来把握他心,并且都通过扩展感知的内涵来说明我们何以能够直接感知到他心。但是,在进一步为这种直接感知的可能性辩护的时候,两者采取了根本不同的思想模式。我们把自然主义的辩护原则称为“自然机制”,而把现象学的模式称为“意义机制”。意义机制一方面有别于先验的辩护原则,有向生活经验层面的回返;另一方面,它又不同于自然机制,它是在经验内容层面寻求经验现象的整体性或统一性原则。自然机制的辩护模式会导致心灵的直接实在论,这种主张将陷入无法区分心物的两难困境。意义机制则与之不同,它通过诉诸自我和他我在社会生活中的构造过程来说明直接感知如何可能,这样做能更好地避免直接实在论带来的两难。
[关键词]他心;现象学;自然主义;直接感知
如何把握他人的心灵是当代心灵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他心直接感知理论是当前学界较为流行的一种,它主张我们能够在知觉层面直接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这一主张与现象学的立场有相通之处,它们都认为对他心的把握是直接的,不需要类比、模拟、移情或其他中介性心理活动的介入。事实上,不少他心直接感知理论的早期提出者有现象学背景,或利用了现象学资源,因而他心直接感知成为现象学与自然主义者共同关注的话题。
对于它们之间的思想互动及分歧,学界已有不少辨析。这些辨析整体而言将现象学的论证方式归诸先验性,从而与自然主义的自然性或实证性的论证方式作出区别。比如,扎哈维(D.Zahavi)指出,现象学的终极目标是提供“先验的(transcendental)哲学说明”,并认为这是它有别于自然主义的地方。(参见Zahavi,2009,p.8)自然主义者也正以先验性为切入点解读现象学的特征及其局限性。(参见Pylyshyn,p.362;王华平,第119页)这个辨析泛泛地说不无道理,毕竟现象学家有时也采用了“先验性”这个术语。但这一解读包含了对现象学的简单化,没有充分顾及它与传统先验哲学的区分。当然,针对自然主义的问题视野,尤其是它的自然化展示路径,现象学也需要采取新的诠释路径来作出回应,而不是简单地重复经典现象学的行话。
下面的讨论将从他心直接感知理论的现象学渊源开始,展示双方在出发点上的共识,即都强调这是一种非推论性的直接把握。而后,本文将结合学界已有的讨论,探讨双方对直接性把握之可能性的深层辩护,并展示双方的原则性分歧。为了更好地呈现这个分歧,我们将双方的辩护原则进行了提炼,分别称为“自然机制”和“意义机制”,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两种辩护机制的得失。“意义机制”的提法有助于避免将现象学混同于先验哲学,可以为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的对话提供新的思想视角。
一 他心直接感知理论的提出及其现象学“渊源”
最早提出并关注他心直接感知理论的学者,比如加拉格尔(S. Gallagher)、扎哈维、卡萨姆(Q. Cassam)、克鲁格(J. Krueger)等,有不同的学术背景,涉及现象学、维特根斯坦哲学以及认知科学等(参见Gallagher,2004,2008;Zahavi,2007,2011;Cassam; Krueger);国内关注该问题的学者也来自不同的领域(参见罗志达;张浩军;王华平;陈巍)。我们这里主要关注该理论与现象学的关系,为此,选择加拉格尔与扎哈维的论述展示该理论的要义,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它与现象学的共识与分歧。下面的讨论将表明,不仅他心直接感知理论的提出——也即在反驳理论论和模拟论方面——“重演”了现象学家的论证思路,而且其对“感知”内涵的拓展也可以被看作对现象学思路的再现。
他心直接感知理论主要是针对当代心灵哲学中两种典型的他心感知理论——理论论(Theory Theory,简称“TT”)和模拟论(Simulation Theory,简称“ST”)——而提出的。理论论主张,民众的日常心理包括各种概念形成的因果原则,构成理论之网,成为我们知道他心存在的理论依据。模拟论指的是以自己的心理状态为摹本,通过模拟的方式来了解他人。加拉格尔指出,这两种理论有一个共同预设,即认为他人的心理状态是某种隐藏着的东西,并不是我们知觉的直接把握对象。对理论论而言,这可能基于一种日常的盲目信念或者基于一种理论设定;对模拟论而言,这基于对自身心理状态的把握,以一种类比的方式把它作为他心的原型。因此,这两种他心感知理论都可以说是推论性把握或间接把握。“我不能看进你的心灵,因此,我必须想出一些方法,根据提供给感知的内容来推断那里一定有什么。”(Gallagher,2008,p.536)因此,这就需要经过一个读心(mind-reading)的过程来把握他心,就像戈德曼(A. I. Goldman)说的,这是一种“心灵对心灵的思考”(Goldman,p.3)。
加拉格尔在现象学以及维特根斯坦哲学相关论述的基础上,提出了直接感知他心的思想观点。与理论论和模拟论不同,他心直接感知理论主张我们在知觉活动层面就能够直接感知他人的心理状态,而不需要经过任何形式的推论或中介。(参见Gallagher,2008,p.535)扎哈维同样指出,理论论和模拟论虽然在描述社会认知的本性方面有一些根本区别,但是它们在身心关系上具有一些共同的基本预设——它们主张人的心灵是隐藏着的,我们不能直接经验到其他生物的心灵,而这些预设在扎哈维看来是成问题的。扎哈维依托现象学家(胡塞尔、舍勒、梅洛-庞蒂等)的论述指出,心灵并不是隐藏在身体背后的实体或幽灵,而可以在身体的表达性行为中直接呈现出来,因而我们对他人的心灵可以有一种直接的经验。(参见Zahavi,2007, pp.31-32)
为了更好地把握他心直接感知理论与现象学的“渊源”,我们简要回溯一下现象学家的相关论述,看看他心直接感知理论在哪些方面“再现”了现象学的基本思路。
胡塞尔在论述交互主体性问题时,对我们如何把握他人的心灵进行过现象学描述。他首先从常识出发表明,当我们把他人看作一个跟自己一样有心灵的存在者时,这一行为看似包含了一种“类比”。但他很快又指出,这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类比。由此他提出了一个现象学的问题:我们如何能够在一种非类比的意义上构造出一个他者,也即如何以非类比的方式把握他者。(参见胡塞尔,2008年,第131页)不仅如此,胡塞尔进一步把这种把握方式称为“感知”。(参见同上,第158页)海德格尔同样反对我们是通过类比或移情来实现对他人的把握的。他认为,这种做法预设了一个人面对自己时与面对他人时的存在方式是不一致的,而这个预设是不成立的。(参见海德格尔,1987年,第145页)海德格尔在跟朋友讨论一个人是否能够完全将自己放到另一个人的立场上去时,援引了《庄子》“秋水”篇末尾庄子与惠施关于我们如何能知道“鱼之乐”的讨论。(参见张祥龙,1996年,第451页)庄子在这里无疑主张,我们是可以直接看出“鱼之乐”的。这里也包含了直接感知他心的基本思路。
舍勒的阐发跟当代心灵哲学的关联更直接。他专门反驳了类比理论与移情说,并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类似“直接感知他心”的主张。
类比理论主张,我们首先感知的是自己表达活动背后的心灵状态,然后通过他人可观察的表达活动,以类比的方式推断出他人具有相似的心灵活动。舍勒指出,类比说存在如下问题:第一,它没有注意到,婴幼儿即使不会进行类比推理,也可能识别出表情背后的东西;第二,我们并不是通过观察来把握自己的表情的,因此也就谈不上通过看到他人相似的表情去推断相似的心情;第三,我们还能看出动物的“心情”,但是人和动物的表情并不相同;第四,类比理论还有一个逻辑错误,它只能推断出同样的表达行为背后有一个类似的“我”,但是,它无法表明这个“我”如何不是“自我”,而是“他我”,也即是说,在我们感知到他心的时候,知道他心不仅类似于自己的心灵,而且有别于自己的心灵,类比理论无法对此种差别作出说明。(参见Scheler,p.234)
移情说主张,自我通过移情的方式进入另一个身体,并由此获得对“他心”的把握。舍勒分析指出,其问题在于它只提供一种关于他心的假定,因为它基于移情造成的一种信念,而这种信念缺乏明见的保证。比如,我们可能因为与死者发生移情从而赋予死者“灵魂”,而这原则上只是一种假设,移情说无法提供这种假设的合法性。因此,通过移情把握到“他心”的存在,可能完全是一种巧合。此外,跟类比理论一样,移情说只是把“自我”放置到其他地方,它只是在他人那里再现对“自我”的体验,而不是感知到“他我”的存在。(参见同上,pp.235-236)
舍勒通过以上分析表明,类比理论和移情说在描述我们如何感知他心的时候都不够原本,都预设了我们已经能够达及他心,从而没有对我们如何把握他心作出正面描述。舍勒对我们如何把握他心作了一个现象学描述。在这个描述中,他明确表示,我们是从他人的表情和姿态中直接感知到他人的心灵状态的:“我们当然以为我们从微笑中直接看到他人的快乐,从眼泪中直接读出他的悲哀和痛苦,从脸红中直接体会他人的害羞……谁要是对我说,这不是‘感知’(Wahrnehmung)······我请求他离开如此成问题的理论,回到现象学事实中来。”(同上,p.254)舍勒接着指出,这种感知不需要推论,是“直接感知”(unmittelbaren Wahrnehmungen)。虽然我们在特定情况下有可能会去推论他人的心理活动,但这种推论都是以素朴的“直接感知”为前提的。(参见同上,p.254)
由此不难看出,他心直接感知理论无论在反驳理论论与模拟论方面,还是在直接感知的主张方面,基本上都在现象学的考量范围之中。它们可能在反驳细节上有所不同,但在拒斥这两种理论所导致的间接性并诉诸知觉获得直接性这个基本的方向上是一致的。就此而论,直接感知理论没有任何新意。
不仅如此,自然主义对“感知”内涵的拓展,也参考了现象学的基本思路。如果我们对他心的感知是像感知日常事物那样直接,这会导致我们认为心就是物或者心乃众多物中的一种,这与我们的常识是有出入的。换言之,我们需要对感知观本身进行重新解释,以此来协调它跟常识或传统感知观之间的不一致。在这方面,加拉格尔采取的做法也与现象学家的思路基本一致,它们都拓展了传统哲学视野中对感知的理解。
加拉格尔表明,人类的知觉活动并不像我们通常认为的那样单一,而是有一个动态的自身调整能力,以此来感知不同层面的东西。比如,视觉在不同环境下的感知能力会发生调整,大家都有这方面的经验。加拉格尔把这个思路推而广之,提出了“巧知觉”(smart perception)的主张。他据此表明,知觉活动的调整范围极大,不仅限于通常的感觉领域,还能够达及人的精神领域。为了更好地展示巧知觉的内涵,加拉格尔把传统的知觉观称为“钝知觉”(not-so-smart perception,直译是“不那么巧的知觉”)。根据钝知觉理论,我们的知觉活动只能接受单纯的感觉材料。以知觉一辆红色轿车为例,我们需要首先感觉到汽车的颜色、形状、材质,而后在此基础上赋予其意义,这样才能把它把握为汽车。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知觉活动的基础上加上一个认知过程才能感知到汽车。巧知觉理论不同,它认为在知觉活动层面内我们就可以直接把它看作汽车。加拉格尔进一步主张,我们不仅能直接感知物的存在(即把某物作为某物来感知),还能直接感知人的心灵状态。他援引发展心理学材料来支持这个主张,比如,婴幼儿在获得任何理论乃至在形成概念之前,就能直接从母亲的表情中感受到她的情绪。(参见Gallagher, 2008, pp.538-539)加拉格尔还从时间化的角度阐发巧知觉的动态适应性特征。他主张,知觉活动模式有一个在时间进程中的变化过程,也就是说,知觉模式不是静态的,过去的生活经验会直接影响我们当下的知觉方式。(参见同上,p.540)这一主张同样得到了认知科学中“高层次感知”理论的支持,后者主张我们不仅能直接感知自然物,甚至社会特征、因果特征、道德特征乃至心理特征等,都可以是知觉的直接把握对象。(参见Helton,p.851)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这一对感知内涵的拓展同样并不新鲜。在笔者看来,加拉格有关巧知觉的描述可以看作胡塞尔感知现象学的一个“简化”版本。胡塞尔将通常钝知觉所接受的感觉印象称为感觉材料,他认为正常的感知活动并不停留在这里,而是能够在接收到感觉材料的同时对它进行“统握”或“立义”,使我们能够直接感知到汽车,而不是颜色、形状。胡塞尔对此种感知活动的展开过程进行了多层次、多方位的细节分析,涉及“统握”“边缘域”“侧显”“共现”“立义”等。加拉格尔有关知觉的时间化特征的论述,可以视作后期胡塞尔有关被动综合思想的朴素表达。胡塞尔明确表示,过去的经验会作为习惯性的知识积淀在意识之中,并指出,这种积淀不只是通过记忆的方式进行间接保留,而是可以在知觉活动中直接体现出来。(参见胡塞尔,1999年a,第146页)舍勒更是很早就利用儿童心理学的材料表明,婴幼儿对表情背后的心灵状态有直接的感知,它不需要类比推论。(参见Scheler,p.233)
可见,现象学家早已拓展了“知觉”的思想内涵,自然主义者有关巧知觉以及知觉扩充理论的分析,并未超出现象学领域有关诸种直观的分析。由此我们可以说,自然主义者所主张的他心直接感知理论无论在立论上(反驳理论论与模拟论)还是在感知现象的描述方面(不同于传统经验主义视野中的感知观念),都没有超出现象学的范围,最多只是换了个名称。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然主义有关他心直接感知理论的所有思考都可以归诸现象学。进一步探讨双方有关直接性的辩护理由可以看到,双方在他心感知问题上其实“貌合神离”。
二 双方辩护原则差异的通常解读:自然性与先验性
现象学和自然主义的差别体现在对他心直接感知现象之可能性的进一步阐释上,从这里我们能看到两者思想旨趣的原则性差别。
我们还是借助加拉格尔有关“巧知觉”的进一步分析来看自然主义如何提供辩护理由。加拉格尔的巧知觉理论是以视知觉对环境的适应性现象为思路而提出的,并把它推广到他心的感知上来。这种推广不是简单的类比,而是诉诸背后的自然机理。他援引脑神经科学来佐证这一主张:产生适应性调节的过程只发生在大脑皮层前部和中部,不涉及构成概念和认知基础的前额叶和顶叶区域。这以实证或科学的方式证明了对他人情绪的感知是一种直接的知觉活动,而不是(高阶的、塑造联想和推理的)认知。加拉格尔解释过去经验如何影响当下的知觉活动时,同样诉诸脑神经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表明这不是认知的影响。一般认为,对事物带有意谓性的感知(也即不止感知到一个东西,而且把它把握为一个有用的东西、一个自己喜欢的东西等)依赖于早期知觉处理区域(比如视觉的V1区)之外的联想脑功能区的激活,我们通过它把过去的经验附加到当下的知觉活动之中。加拉格尔结合最新的认知科学研究指出,即便是早期的知觉处理区域(比如V1区),其神经元活动都超出了单纯的特征捕捉。V1神经元会根据过去的经验调整自己的回应方式。这就表明,过去经验对我们当下知觉活动的影响不只是通过联想以及高层的认知活动造成的,它可以在知觉活动内部直接完成。(参见Gallagher,2008,p.538)
通过上述例子已经能看出自然主义辩护的基本思路:他们不是进一步剖析感知这个经验行为本身,而是以相关现象为出发点,结合认知科学的最新成果,寻找背后的自然发生机理,最终在这样一种客观的发生机制上来证成他心感知现象。为了与现象学的辩护作出区分,我们这里把自然主义的辩护原理称为“自然机制”。换言之,自然主义辩护他心直接感知的最终理由是,我们感知他心的自然机制同我们感知他人身体和其他事物的自然机制是一样的。
现象学没有进行这方面的辨析,不仅如此,进一步考察现象学家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诉诸自然机制来解释“直接感知”的做法正是现象学家所要摒弃的。
胡塞尔在其思想早期就辨明了现象学与自然主义理路的差异。他认为,自然主义尝试对哲学进行严格的“科学改造”这一做法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参见胡塞尔,1999年b,第6页),他本人的意识现象学原则上不同于“意识的自然科学”(参见同上,第18页)。“意识的自然科学”可以视作对当代心灵哲学的一个描述。舍勒同样对诉诸自然机制解释心理活动的做法提出了挑战,质疑人类的心灵活动与身体的自然机制或神经系统之间存在严格的依赖关系。他质疑的关键在于指出,这里存在两种不同的原因。我们心灵活动的经历虽然离不开身体,但它们只是此经历之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此经历之内容的必要条件。比如,依靠视觉系统这套身体性装置,我们才可以看到太阳、月亮。但是所看到的内容(比如太阳、月亮及其感性特征)并不能通过视觉系统来得到完全说明,这是两个不同层面的东西。心灵经验的获得固然离不开大脑神经系统的支持,但神经系统只是心灵经验的外部条件,不足以说明心灵经验的内容本身,它们之间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参见Scheler,p.248)
当然,这不意味着现象学就要违背科学,认知科学的最新发现也可以用于解释现象学。知觉科学家有关视觉神经元功能的发现可以用于“佐证”海德格尔的讲台体验分析,表明我们如何能一开始就把讲台看作讲台,而不需要先获得讲台的感觉印象再通过认知过程才把它看作讲台。镜像神经元的发现也可以用于“佐证”舍勒对他人情感的感知的分析。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更是大量借用心理学、知觉科学的实验现象。不过与自然主义不同的是,现象学不会止步于心理学、认知科学提供的科学证据。现象学家面对这些科学性“现象”的时候,还尝试对此“现象”之可能性作出进一步追问,提供出新的“解释模型”。
就他心感知问题而言,现象学在剖析完“直接感知”现象之后往往诉诸若干“先验性结构”,比如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海德格尔的共在以及梅洛-庞蒂的具身主体等,把它们作为上述现象能够出现的可能性条件。扎哈维已经注意到并指出了双方在这里存在辩护原则的差异,他说现象学家关注的是“事情本身”,而认知科学家处理的是“实在的机制”。(参见Zahavi,2007,p.554)但是,“事情本身”依然是一个现象学行话,这种辩护无法让自然主义者信服。那么,“事情本身”究竟是一种经验性内容还是一种先验内容?
另外,不少自然主义研究者也都看到了这种表面的相似性,并着眼于从先验性视角对现象学分析所给出的“直接性”理由进行反驳。在他们看来,现象学的辩护并不彻底,它不能真正区分不同的经验来源,从而无法完全刻画直接感知理论的特征。派利夏恩(Z. Pylyshyn)指出,从现象学所立足的“主体经验”出发不能确定经验的来源是视觉系统还是我们的信念。(参见Pylyshyn,p.362)在他看来,现象学所谓的直接经验内容可能是知觉经验和知觉信念共同作用的产物,这就不同于自然主义的直接感知。高普尼克(A. Gopnik)还指出,这里有可能存在所谓的“专家效应”,也即专业知识会直接造就新的直接经验模式,你以为属于直接经验的,其实已经暗中基于专业知识进行了推理。(参见Gopnik, p.336)
从这里能看出,自然主义者也从原则上拒斥现象学的深层辩护,认为它们是不彻底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交互主体性、共在、具身主体等概念上,并把它们理解为一种先验性结构或原理,那么,现象学的辩护依然跳不出自然主义的批评。事实上,塞尔(J.Searle)曾从自然主义立场出发对现象学的思想方法有过一般性的批评。在塞尔看来,现象学通过反思性的思想方法去解释意识结构(这里主要指胡塞尔现象学),这跟传统唯心主义的思路是一致的,也就是将物的存在还原为一些先验意识所构造的“实在”。(参见Searle,p.116)这个批评也可以用到他心问题上。在自然主义者看来,广义的读心现象学关涉的是“构成性先验问题”,而自然主义的他心直接感知理论关心的则是“读心的过程和机制”这样的自然主义问题,所以两者不是同一个层面的思想。(参见王华平,第119页)这里我们还可以接续自然主义视角对现象学的辩护提出进一步的批评,也即现象学的辩护看起来在回答而实际上回避了问题:它将我们在经验层面需要回答的问题,也即在经验行为中如何通达他心,切换到先验层面,变成了我们与他人在先验层面本来是同一个“主体”、同一个“心灵”,或把“主体”替换为“交互主体”,从而消解掉如何在经验层面通达他心的问题。
因此,自然主义对现象学的可能批评,不仅涉及双方的分歧,也对当前的现象学研究提出新的要求。我们有必要接着自然主义的视角,进一步审视现象学的解释模式,看看它到底有没有正面回答通达他心的问题。
三 现象学辩护原则的进一步阐释及其与先验性、自然机制的区别
我们先把交互主体性、共在、具身主体等现象学“大概念”放在一边,看现象学家如何具体分析我们对他心的把握。在具体路径上,不同的现象学家也有不同视角,我们这里以舍勒的分析为例展开讨论。
舍勒在分析类比理论的时候探讨了其错误的根源,即它从一开始就假定了一种错误的心灵给予方式。类比理论往往主张,最先呈现给我们的是本己的自我,他人直接呈现给我们的是他的身体表象和身体动作,我们只能经由他人的身体表象去把握他心。在舍勒看来,这个看似自明的出发点已经预设了很多,且从一开始就误解了心灵的原初给予方式,从而陷入了诸种理论困境。
舍勒接着对此种“预设”进行了现象学的悬搁与还原。他分析指出,自我与他我首先都共同生活于一种不分你我的生活流之中。这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和经验成为后来每个自我建构出自身的基本材料。也就是说,“自我”不是通过“反省”自己的内心活动来把握自我的,自我是在与他人共同的生活经验中逐渐成形的,也因此是以共同生活为基石建构出来的。这一点可以从婴幼儿和各民族早期的原始心灵状态看出来。一个孩子早期的“心灵活动”是和他的周围世界(包括他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他们所属的生活方式、文化传统等)融合在一起的,他个人的“精神追求”完全融合在此种共同生活之中。随着他心智的成熟,才逐渐与此种生活共同体拉开“距离”,并形成“自我”的观念。早期人类的人性结构也是如此,他们的“自我”观念与原始部落的“群体意识”深度融合在一起。“自我”意识形成的过程乃是与此种共同体分离的过程。这就同时表明,“自我”不是隐藏在身体内部,而是本来就出自共同生活经验。我们能够像直接把握自我那样去把握他我,因为自我和他我都出自那个大家一开始就归属于它的“共同生活”。换言之,组建自我和他我的“材料”本来就是公开的,为大家所共有,因此,也就不存在我们如何能够透过身体去把握其“内心”的他心感知难题。
虽然不同的现象学家在如何感知他心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具体进路,但整体而言,都可以说是通过重构心理体验与归属者的关系来回应他心感知问题,比如梅洛-庞蒂的具身主体性可以视作对身心如何无缝链接为一个整体的现象学描述,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海德格尔的共在也都尝试通过重构“主体性”来说明他心感知如何可能。他们都主张在自我的主体性建构过程中,他我已经涉入了。正是这种自我跟他我在构造过程中的“同根性”,才使得我们能够直接感知他心。
那么,这种“同根性”是不是德国唯心论所诉诸的先验性呢?这样说也无不可,现象学确实接取传统先验哲学的思路追问和探寻经验内容的可能性条件,他们有时还直接使用了“先验性”的字眼。为了更好地回应自然主义视角的批评,也为了更好地展示现象学的辩护原则与先验哲学的区别,我们这里把现象学所追问的可能性条件称为“意义机制”。
“意义机制”是张祥龙用现象学方法分析中国哲学问题时首先提出来的,它被用于刻画人生意义的发生根源。(参见张祥龙,2019年,第231页)在笔者看来,它可以更一般地用于刻画现象学的思想诉求。胡塞尔通过现象学还原所揭示的意识活动主要是一种赋义活动,此赋义活动所构成的“意向对象”在根子处已经具有“意义”的基本特征。“一切实在的统一体都是‘意义的统一体’。”(胡塞尔,1992年,第148页)舍勒通过区分感觉以及对感觉的感受来建构他的价值伦理学。我们对感觉的感受可以被理解为感觉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参见舍勒,第19页)海德格尔的思考介于胡塞尔与舍勒之间。他一方面以西方的存在论思想为切入点,另一方面又以人的生存为根基,并以“存在的意义”为纽带将这两方面关联为一个整体。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则可以说为“意义”提供了一个“肉身”。“意义”不再是抽象的观念对象或附属物,而是我们可以具有身体性感受的直接内容。他从不同层面表明,意义的生成如何总已伴随并先于感觉经验和理性判断。(参见梅洛-庞蒂,第44、61—62页)由此可见,现象学家以不同方式指向了一种源发的意义生成现象或意义机制。“意义”先行于又关涉于认知真理、伦理价值与审美体验,贯穿于不同的思想领域。
相比于康德哲学中的先验形式,现象学家所揭示的意义机制更“内在”于经验活动。胡塞尔曾指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中的先验演绎已经是在现象学的基础上运作了,但是,康德由于将它误解为心理学的,最终放弃了它。(参见胡塞尔,1992年,第161页)舍勒同样通过与柏拉图、康德的先天论对话表明,现象学所揭示的“先天”关涉一种奠基性的构造性活动,而不是康德那种先验意识形式。(参见舍勒,第59页)海德格尔在《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中同样接取康德主观演绎中的基本思路来展示时间意识如何先行提供出经验行为的“对象”,也即存在者之为存在者的“意义”。海德格尔指出,康德对感性经验条件的展示是不够的,康德所论述的感性化只是一种“有限直观”,它不能提供出存在。(参见海德格尔,2011年,第86页)在梅洛-庞蒂看来,康德哲学中的先验形式已经是对现象的解释和抽象了,已经“远离”了现象自身。(参见梅洛-庞蒂,第4页)因此,现象学所要揭示的“意义机制”与康德所揭示的作为经验之可能性条件的先验形式有关键的区别。康德的先验哲学最终诉诸一种形式的先验性,虽然它被归诸先验主体,但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关联,主体的“价值”无论在先验的感性形式中还是知性范畴中都得不到体现,因为它们完全可以作为自在的时空形式和逻辑规律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先验形式事实上已经从经验中“剥离”或抽象出去了。
此外,意义机制与自然机制也有根本的区别。虽然它们都试图透过经验现象揭示其背后的普遍化“机理”,但是,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自然机制只是经验活动的一个“外部”条件,意义机制则不同,它在经验内部运作,更直接地构成了经验活动的“动因”。没有眼睛、没有视觉神经元,我们不可能看到任何东西。但是,当我们被美景吸引的时候,打动我们的是美景在经验层面给予的“内容”,而不是神经元对物理刺激的自然反应。换言之,这一物理刺激的过程并不是我们的经验内容。与自然机制不同,意义机制跟我们当下的心情乃至过去的生活经历都有关系,这些内容都是可经验的。现象学尝试揭示的是此种关联的意义-机制,而自然主义关注的是大脑皮层受外部刺激的一个信息接收与条件反射的自然机制。
诉诸自然机制来解释心理现象本质的做法看起来很科学,不插入任何形而上假设,直接描述可被观察的事实本身。但这种做法没有意识到,经过如此揭示,自然机制本身已经脱离了人的“经验”。人害羞时会脸红。对于脸红的原因,自然主义者倾向于揭示出大脑皮层在接收到某些刺激时会作出某种回应,并以此让脸部毛细血管充血。这是“脸红”的自然机制。但它描述了我们的害羞-经验吗?事实上,扎哈维在深入辨析现象学与自然主义关系的时候,已经暗示了这样两种机制的差别,表明现象学的辩护从经验对于主体的“意义”来理解,而不是像自然主义那样考察亚人的机制(subpersonal mechanisms)。(参见Zahavi,2009,p.8)扎哈维这里论及的从经验对主体的“意义”来考察经验,已经具有意义机制的意味,只不过他没有完全说出来,而是将之归诸第一人称视角。“意义机制”的提法与第一人称视角不完全相同,它在某些方面也可以是第三人称视角的。比如,张祥龙以棋类游戏的机制——它依循一定的规则,但可以在游戏中不断翻新,带来新的意义感受——为例来展示意义生发结构(参见张祥龙,2022年,第8页),我们不能说这种展示是第一人称视角的。如果说康德哲学的先验形式从经验“内部”方向脱离了经验,那么,自然机制可以说从经验“外部”脱离了经验。其结果是一样的,都错失了经验活动本身。意义机制则与它们不同,它并不脱离经验,但又不止于经验的表层,而是在经验之中显示此种经验何以可能的机制。
我们回到他心问题,以意义机制为视角,展示现象学家之辩护的要义。下面以常被自然主义者指责的海德格尔思想为例。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表面看来好像跳过了如何通达他心的问题,因为他主张自我不是单子式的绝缘体,世界一开始就是众多自我共同在此,因而也就不存在自我如何通达他我的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停留在表面,需进一步考察他对共在的界定。事实上,海德格尔正面探讨了我们是如何与他人“照面”的。按照他的分析,在日常操劳活动中,“他人”是随同我们日常操劳所及的物件、器具一起来与我们照面的。我们看到一条小路、一只小船的时候,都已经暗中“照面”了他人。这并不是说,由小路、小船联想到一个具体的作为人的物件。海德格尔指出,我们照面他人的方式不同于照面普通的物件,他人跟我们自己一样,都不是现成的存在者,而是具有世界性的存在方式。换言之,这个世界不只对“我”敞开,同时也对“他人”敞开。正是以世界的敞开性为中介,自我才跟他人共同在此、共同在世界之中存在,因为“此在”本质上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由此,海德格尔明确反对那种首先把“自我”和“他人”各自封闭起来,而后考察自我如何达及他人的提问方式。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自我与他人本就是“共根”的,共同在一个世界之中存在。(参见海德格尔,1987年,第137—138页)
然而,上述回答不还是回避了问题吗?以意义机制为视角,可以更好地看到海德格尔在心灵现象展示上的推进。海德格尔这一辩护的要义在于反对“心灵是隐藏在身体内部的某种独特现象”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每个人只能透视自己的心灵。在反对这种幽灵式、单子式心灵观方面,海德格尔跟自然主义的路径是一致的。海德格尔比自然主义更激进的方面在于,他不仅不认为心灵是隐藏在身体内部的“幽灵”,甚至也不认为心灵是附着在身体表面的伴生现象,而认为心灵就是敞开在整个“世界”现象之中的。我们能通达一个世界,就意味着我们已经通达了“心灵”现象。这既包括对自我的通达,也包括对他我的通达。对于海德格尔,正是这种“通达”或可通达性本身构成了原本的心灵现象。按照海德格尔的思路,人对自我的认知并不是通过反思性的观察得来的,而首先是通过在世的操劳活动来展开的,对他我的认知也是如此;这种日常的操劳活动一开始并不分你我,是同时向大家伙“敞开”的。(参见同上,第144页)由此可见,海德格尔回应通达他心问题的要点在于指出,心灵现象并不是隐藏在身体内部的幽灵,而是表现在操劳活动之中,既然我们能直接通达操劳活动,那么我们就能同时直接通达“心灵”现象。与舍勒诉诸“共同生活”类似,海德格尔也通过对心灵现象的还原来展示不同心灵相互通达的可能性,其还原也是朝向具体的共同生活经验,它们是心灵的原始开展活动。如果说自然主义尝试通过揭示脑神经的自然机制来展示心灵现象的实质,那么,海德格尔或一般的现象学家则是通过展示“心灵”在生活经验中的发生过程——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意义机制——来展示心灵本身。
由此可以看到,现象学的辩护不是诉诸康德哲学式的先验原则,相反,它诉诸的是一种原初的经验现象。但又不同于自然主义,它并不寻求经验背后的自然机制,而是尝试在“经验现象”中显示作为其“原理”的现象的统一性、整体性机制,也即意义机制。
四 两种辩护原则的得失
结合上述讨论可以看出,自然主义者所理解的充分辩护需要提供知觉经验的自然机制,它更多地倚重并结合最新的认知科学,给我们理解心灵现象提供新的进路。可以设想,由于这种自然机制从认知科学而来,因此它与人工智能可以有更多契合之处。现象学不那么倚重认知科学,这方面是它相比自然主义的不足。但就哲学研究而言,这个不足恰恰构成了现象学相比自然主义的优势,因为心灵现象具有非实证性特征,而自然主义对实证性的过度倚重使其对心灵现象的展示流于“表面”。
如上所述,自然主义用以辩护他心直接感知的最终理由是自然机制的同一性,也即感知心与物的大脑神经元反应机制是一样的。他们由此明确主张,我们像感知物一样感知他心。根据塞尔的知觉观,我们的知觉所直接把握的并不是感觉材料,也不是有关实在的“表象”,而是实在本身,他称之为“直接实在”。(参见塞尔,第227—228页)自然主义研究者也据此表明,我们所把握到的心灵状态是“直接实在”而不是“间接实在”。(参见王华平,第81页)但是,这个思路会暗示心物就是同一种实在,或者至少是同一类型的实在,差别无非在于实在的样态。由此而来的疑问是,既然我们看见他人身体和看见他人心灵的自然机制是一样的,那么由此被看见的“心灵”是否和“手脚”是同一类实在呢?如果不是,区别在哪?面对这些问题,自然主义会陷入两难:如果抹去这些区分,这种直接实在论会陷入与常识的冲突之中,毕竟,没有人会接受心灵跟身体是同一种实在;如果要对心物的不同实在性作出进一步解释,按自然主义的思路,还需要进一步寻找自然机制的差别,但是那样一来,就会导致直接感知理论的破产。
自然主义感知理论面临的两难表明,心物关系恐怕很难在感知它们的神经元功能层面得到完全的说明,而这些地方正是现象学的思想立足点。结合我们前面有关海德格尔共在问题的解读可以看到,现象学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个问题。虽然现象学家主张我们能够直接把握他心,但是这两种把握方式的意义机制是不一样的。
不仅如此,从现象学的角度看,他心直接感知理论虽然批评了理论论和模拟论,但它们在理论出发点上存在共同性,即都把心灵活动视作身体的“伴生现象”(Epiphanomenalismus)。其差别无非是,理论论和模拟论认为他心隐藏在身体表象内部(可以理解为“内生的”,所以看不见),而直接感知理论主张他心附着在身体表象之中(可以理解为“外生的”,所以是一种“直接实在”)。现象学的视角则不同,它不认为“心灵”是单纯的身体伴生物,而强调它同时还是一种共同的社会生活产物。并且,正是这种共同性或共根性才使得我们可以直接通达“他心”。我们有时候可以不通过身体而直接把握“他心”,甚至能够从他人留下的精神性活动的符号或踪迹中直接感知他心的在场。比如,我们可以从古人的文字中直接把握古人的“精神状态”,而无需通过其身体,这种把握很多时候比观看身体来得更直接、更真切。可见,“心灵”并不是身体的直接伴生物。(参见Scheler, pp.251-252)
在他心问题上,考虑到自然主义者把他们的立场称为直接实在论,以此有别于理论论或模拟论这些间接实在论,我们在此暂且把现象学诉诸意义机制所展现的他心存在方式称为“构成实在论”。构成实在论有别于间接实在论,不认为他心是通过推论获得的间接实在。它也有别于自然主义的直接实在论。虽然它主张在感知他心的过程中有一种知觉的直接性,但它不认为此种直接性跟感知自然物的直接性是同一类直接性;它在自然感知的基础上还有一个意义构成环节,自我和他我都是此种意义构成的产物。
现象学的构成实在论还有别于传统先验哲学的先验实在论。先验实在论不考虑“自我”和“他我”在经验生活中的“发生”过程,只是从先验形式层面揭示一种关联的可能性,不触及他心问题在经验层面的产生过程。构成实在论则不同,它基于社会生活过程中的行动与交往,把“心灵”现象跟这个行动交往过程关联起来思考,并由此表明,对他心的感知是一个通过与他人(包括他人留下的语音文字以及其他社会性产物)的交往互动过程进行“构造”的过程,对他心的把握是此种构造的产物。
自然主义与现象学这一思路的区分可以追溯至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年轻的时候被阿那克萨戈拉吸引,因为后者说“心灵”是安排一切的原因。苏格拉底满怀希望地跑去向阿那克萨戈拉学习“心灵”哲学时,却非常失望,因为虽然阿那克萨戈拉把心灵作为一个人行动的原因,但他在进一步解释此现象时却诉诸人的身体结构。苏格拉底认为这不是他所关心的“原因”:“他也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说明我同你谈话的原因,把它归之于声音、空气和听觉。他可以指出一万种诸如此类的原因,却忘却了那真正的原因······”(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第63页)苏格拉底这里区分了两种原因:一种是行动的外部条件,即“骨头”“肌肉”等;还有一种是行动的内部原因,也就是苏格拉底“认识你自己”所要朝向的人的“心灵”现象。现象学家对心灵现象的分析接续了苏格拉底的思想,自然主义者则尝试回到阿那克萨戈拉,只不过把骨头、肌肉换成了神经元。如果说先验形式从经验内部脱离了经验的内容本身,那么自然主义所诉诸的自然机制可以说是从经验外部出发对经验活动何以可能的审视,因此从外部脱离了经验。
结语
以上讨论表明,当代心灵哲学领域中他心直接感知理论提出的动机虽然与现象学有某种相似性,甚至有一定的渊源,但这种相似仅是表面的,双方在辩护原则上有根本的分歧。我们将这种分歧解读为自然机制与意义机制的不同,以避免将现象学视角简单归入先验哲学的框架之中。通过对比自然机制和先验性,我们将意义机制揭示为一种立足经验内容并对经验现象之统一性作出解释的思想视角。
就他心感知问题而言,相比现象学,自然主义的直接感知理论优势在于吸取认知科学的理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新的问题视野,尤其是可以与人工智能研究建立直接的关联。但它背后的实证性立场同时构成了自然主义的劣势和盲点,使它无法真正接取并深化传统西方哲学在身心问题上的思想资源。现象学诉诸的意义机制则不同,它从“心灵”现象的社会发生过程中揭示其“根源”,从而可以将他心感知问题与伦理、审美以及其他的社会文化现象关联起来,提供新的视角,以实现对传统身心哲学的改造与推进。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1981年:《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
陈巍,2021年:《看见他心:从胡塞尔、梅洛-庞蒂到社会神经科学》,载《学术研究》第6期。
海德格尔,1987年:《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王庆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胡塞尔,1992年:《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
1999年a:《经验与判断》,邓晓芒、张廷国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年b:《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商务印书馆。
2008年:《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张宪译,人民出版社。
罗志达,2020年:《社会认知与同感现象学》,载《现代哲学》第1期。
梅洛-庞蒂,2001年:《知觉现象学》,姜志辉译,商务印书馆。
塞尔,2019年:《心灵导论(修订译本)》,徐英瑾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舍勒,2017年:《哲学与现象学》,倪梁康、罗悌伦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王华平,2021年:《他心的达及问题与直接感知理论》,载《哲学研究》第2期。
张浩军,2021年:《理解“Einfühlung”的四条进路——以利普斯为核心的考察》,载《哲学研究》第10期。
张祥龙,1996年:《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9年:《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儒家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2022年:《中西印哲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Cassam, Q., 2009, “Knowing and Seeing: Responding to Stroud’s Dilemma”, in Europe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17(4).
Gallagher, S., 2004, “Understanding Interpersonal Problems in Autism: Interaction Theory as an Alternative to Theory of Mind”, in Philosophy, Psychiatry, and Psychology 11(3).
2008, “Direct Perception in the Intersubjective Context”, in Consciousness and Cognition 17.
Goldman, A. I., 2006, Simulating Minds: The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of Mind Read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opnik, A., 1993, “How We Know Our Minds: The Illusion of First-Person Knowledge of Intentionality”, in A. I. Goldman (ed.), Readings in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Helton, G., 2016, “Recent Issues in High-Level Perception”, in Philosophy Compass 11 (12).
Krueger, J., 2012, “Seeing Mind in Action”, in Phenomenolog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11.
Pylyshyn, Z., 1999, “Is Vision Continuous with Cognition? The Case for Cognitive Impenetrability of Visual Perception”, in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22(3).
Scheler, M., 1973, Wesen Und Formen Der Sympathie, Bern: A. Francke AG Verlag.
Searle, J.,2008, Philosophy in a New Century: Selected Essays,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Zahavi, D., 2007, “Expression and Empathy”, in D. D. Hutto and M. Ratcliffe (eds.), Folk Psychology Re-Assessed, Dordrecht: Springer.
2009, “Naturalized Phenomenology”, in S. Gallagher and D. Schmicking (eds.), Handbook of Phenomen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Dordrecht:Springer.
2011, “Empathy and Direct Social Perception”, in Review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 2(3).
来源|哲学动态杂志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