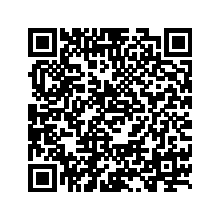[1] Einheit这个术语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汉译本中,译者一般会根据其对上下文的理解而译作“统一性”或“单一性”。 由于本文的讨论恰恰涉及Einheit在康德使用中的含义微妙且重要的差异,为避免因采用不同汉译名可能会给读者带来的先入之见,所以一律将之译作“统一性”。 统一性可以有单一性的意思,反之则不然。
[2]给出了A对应的康德文本(标有文本完成的年代)有以下几种。 《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第1版,1787年第2版;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4-65页(A70/B95),第71页(A80/B106)。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21,1783年;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05-306页。 《形而上学(Mrongovius)》1783年; Immanuel Kant,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Hrsg. von der Königlich Preuß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Berlin: Walter de Gryter (以下简称“Ak.”), Bd. XXIX, Hälfte 1, Teil 2., 1983, S.801-802。 给出了B对应的康德文本有以下几种。 《反思集》(第4700条),1773-1775年; Ak. XVII, 1926, S.679。 《形而上学(Volckmann)》,1784-1785年; Ak. XXVIII-1, 1968, S.396。 《形而上学(von Schön)》,年代不详; Ak. XXVIII-1, 1968, S.480。 《形而上学(Dohna)》,1792-1793年; Ak. XXVIII-2.1, 1970, S.626。 《形而上学(Vigilantius)》,1794-1795; Ak. XXIX-1.2, 1983, S.985。
[3]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75页(B110-111)。
[4] Erich Adickes, Kants Systematik als systembildender Factor, Berlin: Mayer & Müller, 1887, S.42-43.
[5] [英]斯密: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解义》,韦卓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229-230页。
[6] [德]赫费: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现代哲学的基石》,郭大为译,北京: 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26页。
[7] Felix Grayeff, Deutung und Darstellung der theoretischen Philosophie Kants. Ein Kommentar zu den grundlegenden Teilen der Kritik der reinen Vernunft, Hamburg, 1951, S.107.
[8]邓晓芒: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句读》上,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4-305页。
[9] Manley Thompson, “Unity, Plurality, and Totality as Kantian Categories”, The Monist, APRIL, vol.72, no.2, 1989, pp.168-189.
[10] [加]华特生: 《康德哲学讲解》,韦卓民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114-115页。 齐良骥: 《康德的知识学》,北京: 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23页及该页上的注释。 齐良骥所引用的《判断力批判》“导论”中的话表明了康德的三分法排列顺序的根据: “1)条件,2)一个有条件者,3)从有条件者与它的条件的结合中产生的概念”。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第207页。
[11]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86页(B128)。
[12] Von Michael Frede & Lorenz Krüger, ‘‘Über die Zuordnung der Quantitäten des Urteils und der Kategorien der Größe bei Kant’’, Kant-Studien, vol.61, 1970, S.28-49.
[13] Béatrice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Charles T. Wolfe, tra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248-249. 在这个注释中,康德有“当我(在单称判断中)从统一性开始,并这样向全体性前进时”之说。 参见[德]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李秋零主编,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14]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65页(A71/B96-97)。
[15]最后这一点康德并没有在这段引文中直接说出,但无论从这段话的上下文还是从康德在其他许多地方的论述(这些论述中有些在本文后面将会被提到,如《导论》§20中的那个注释),都可知这是其中固有之义。
[16]这里根本不考虑全称判断的主词的外延是有限元素构成的集合的情况,因为超绝逻辑或超绝演绎的论域无疑只是那些真正普遍的认识,如科学的命题甚至于科学的普遍规律。
[17]对于康德在《批判》中所采取的A对应,奥苏里凡也有类似的理解。 参见John M. O’Sullivan, Vergleich der Methoden Kants und Hegels auf Grund ihrer Behandlung der Kategorie der Quantität, Berlin: Reuther & Reichard, 1908, S.60-61。
[18]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465-466页(A582-583/B610-611)。
[19]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426-427页(A523/B551)。
[20]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29页(B39)。
[21]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364页(A431/B459)。
[22]参见[德]康德: 《判断力批判》,《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第189-190页。
[23]关于康德所理解的人类认识模式之为溯因推理,以及在此模式下科学定律是可能的但其确证是不可能的(即它们是可错的),参见钱捷: 《头上的星空——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与自然科学的哲学基础》,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第二部分,特别是其中的第二章“判断力的功效——论康德对休谟问题的回答”和第四章“什么是康德的‘第二类比’? ”。
[24]在今天的康德研究中,有不少诠释者或清楚或含混地断定范畴是由“判断的逻辑机能”产生的,同时对于这种“逻辑”的理解从根本上说却只在于普通逻辑。 龙格奈丝对于康德的“判断的能力”的系统阐述是这种观点的代表,它将这种观点推到了极端,以至于将范畴置于了从属于判断的形式的地位。 参见Béatrice Longuenesse, Kant and the Capacity to Judge。 结果使得阿里松向她质问道: “范畴都上哪儿去了? ” Henry E. Allison, “Where Have all the Categories Gone? Reflections on Longuenesse’s Reading of Kant’s Transcendental Deduction”, Essays on Ka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这种对于康德的理解与本文所阐述的观点无疑是对立的,从而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25]如上节所述,这一点从《批判》中紧接着判断表所给出的对于量的契机的三分法的辩护就可看出来,既然在那里康德首先就说明了传统的普通逻辑对于判断形式的分类是依据类的视角的。 这个视角对于排序的支配(将全称判断列在首位)还可从《导论》§20的那个注释中康德所言看到: 传统的普通逻辑只是将特称判断当作全称判断的“例外”。
[26]更早的《反思集》(第4700条)所采取的B对应正是基于这一视角,虽然那时康德很可能还没有系统地形成他的形而上学演绎。
[27]第二版的“超绝感性论”的“空间概念的形而上学阐明”中说得也许更清楚: “没有任何概念本身能够被设想为仿佛把无限数量的表象都包含于其中的”。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29页(B40)。
[28]顺便指出,在这个注释中,康德表示愿意用“复称判断”(judicia plurativa)取代“特称判断”(particularia),其原因就在于他明确地采取了集合的视角。
[29] [德]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4页。
[30]《形而上学(von Schön)》的年代未能确定,但估计是1780年代末期。 参见Steve Naragon, “The Metaphysics Lectures in the Academy Edition of Kant’s gesammelte Schriften”, Kant-Studien 91. Jahrg., Sonderheft, 2009, pp.189-215。
[31]例如,在全称判断的情况下,主词的外延的潜无限性会带来不确定性(它具体表现在判断的可错性上); 而在无限判断的情况下,则如康德所说: 其主词“被放在这无限领域中剩余的地方。 但这个剩余的地方……却仍然还是无限的”。 [德]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第66页(A72/B98)。
[32]参见[德]康德: 《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329页。
[33]就在《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出版的同一年的8月26日,康德在给舒尔茨(Johann Schultz)的信中赞赏后者独立地意识到这种三段式关系的同时,曾隐晦地表示了范畴的这种性质包含了某种重要的发现,但自己在这方面无能为力甚至看不清它的真实面目。 [德]康德: 《彼岸星空——康德书信选》,李秋零译,北京: 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第135-136页。 另外,关于黑格尔的辩证逻辑的非构成性,可参见钱捷: 《超绝发生学原理》第1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0章第2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