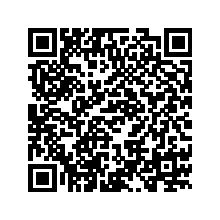学术资讯|我系罗志达教授发表文章:身体空间与儒家的“亲-疏”观念

身体空间与儒家的“亲-疏”观念
罗志达 / 文
摘要
借助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特别是他关于身体之功能性和导向性的分析,该文提出一种初始的“身体空间”,由此进一步澄清传统儒家中基于“身(体)”这一基本范畴的有关“亲-疏”的讨论。
关键词
身体;
一、导 言

▴
胡塞尔
本文的主要工作是借助胡塞尔的身体现象学,特别是基于功能性身体的导向性空间,以刻画一种初始的“身体空间”,进一步澄清儒家思想中基于“身(体)”这一基本范畴所延伸出来的有关“亲-疏”的讨论。
本文不想介入传统儒家如何因应社会生活之现代性转型这一复杂议题,而是关注这个论辩所关涉的一个核心议题:
为此,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二、本己身体与“亲-熟-生”三重关系
在赵汀阳对儒家政治学的批评中[5],其着眼点是传统儒家的思想体系能否提供一个普遍的、基于规则的社会秩序学说,即一种基于任意一个人与任意陌生人关系的基本社会形态。
其一是“陌生人”议题。
其次是“普遍性”议题。
基于上述两个标准和评判,赵汀阳认为儒家与现代社会“本质上是不兼容”的,“儒学的 最大挑战 是没法解释‘陌生人’的问题”。
作为回应,陈少明在《亲人、熟人与生人——社会变迁图景中的儒家伦理》一文为儒家伦理的现代意义提供一种回溯性的辩护[12],其核心是针对上述“陌生人议题”,从“亲亲”关系的普遍性来辩护儒家伦理的核心价值。
首先,陈少明对“陌生人”的性质做了进一步界定:
其次,在这种陌生人构成的社会中,“亲亲”的原则真的失效了吗?
与赵汀阳基于“身体”的有限性来批评儒家伦理学说的局限一样,陈少明也注意到:
这反映了《大学》所呈现的早期儒者看待身体在构建本己与家庭、国家乃至世界之间关系时的基本作用:

▴
陈立胜:
因此,不管是批评儒家的伦理学说,还是辩护儒家的伦理学说,儒学从一开始对本己与世界关系的理解,其落脚点都在“身体”上。
三、基于胡塞尔身体现象学的考察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引入胡塞尔的身体理论,并不是提供一个现象学与传统儒家关于身体的比较研究。
(一)胡塞尔论功能性身体
不同于西方哲学传统中身体研究的模式,即把身体当做一种有待研究的特定课题、对象,因而在其研究框架中已然潜在地采取了一种观察性视角,胡塞尔对身体的分析总是就其在(感知)经验中所起到的功能性作用而展开分析的。
第一,任何感知经验原则上都是源自“第一人称视角”,而不能从一个“无所依的视角”展开。
其次,身体还是一个能够自我触发、自我移动(Ich-bewege-mich)的身体;
那些经历着延展的统觉的感觉是被那些它们现实或可能发生的过程所激发的(motivated),这与一个促动(motivating)序列、与动觉感觉的系统以统觉的方式相关联着——后者在其亲熟的秩序范围内自由地展开着,以至于如果这个系统的一个序列的自由展开发生了(例如眼睛或手指的任意移动),那么从其作为动机的互为编织的复多性出发,一个对应着的序列就作为被激发的[序列]出现了(Hua 4/57-58)。
最后,身体构成自身与世界之间的一个中介(Mittel)或转折点(Umschlagspunkt)。
(二)身体空间、导向空间、同质性空间
基于上述对身体之功能性作用的分析,胡塞尔进一步讨论了由身体所刻画的“导向性空间”(oriented sphere)及其性质。
根据胡塞尔的分析,我们需要区分出导向性空间和同质性空间(homogeneous space)。
与同质性空间相对的则是导向性空间,即一个由本己身体出发的、可以区分出前后、左右的空间。
另外,基于身体的自发移动性,我总是可以把空间上的“那里”转变为“这里”,从而去通达那些远处或多或少模糊不清的景观,后者构成了导向性空间中的“远域”。
(三)身体空间与圈层扩展:
显然,胡塞尔基于对身体之功能性作用的分析,对身体性的导向空间做了进一步界定:
首先,最内核的本己身体空间并不是一个“外部空间”,而是由动觉感觉所塑造的、对于本己身体不假思索、前反思意义上的直接亲知。
其次,导向性空间乃是本己身体的一个切近空间,从感觉模态上说,它首先是可触及的、可直接把握的空间。
如果上述对身体空间之分层结构的描述是适当的,那么对早期儒家而言,其生存经验也具有这种素朴的由近及远的扩展过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易传·系辞下》)。
最后,与上述导向性空间相对照的是客观化的同质性空间。
然则,胡塞尔恰恰在《观念II》中提醒我们,进入这样一个普遍的同质性空间就意味着某种“自我的遗忘”(self-forgetfulness)(Hua 4/183-184)。
四、几个观察

▴
赵汀阳
基于上述关于身体以及身体空间的讨论,我们可以对赵汀阳所提出的“陌生人议题”和“普遍性议题”作出更精确的界定,并基于身体经验及其圈层结构,进一步辩护儒家伦理学说中“亲亲”关系之于陌生人关系的优先性。
在赵汀阳对儒家的批评中,一个重要论点是:
然则,依据上文的讨论,赵汀阳的判断至少有两个方面是值得商榷的:
一方面,如果我们对儒家伦理的起点即“亲亲”做一些限定,它虽然首先表现为一种血缘性的人伦关系,但其真实的经验来源是一种更基础的身体经验。
另一方面,赵汀阳认为儒家伦理植根于“有限的实践条件和地方性语境”,因此它原则上不能成为普遍有效的理论,它针对具体场景中、具有不同身份的人格总是采取有所差别的解释策略。
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做出区分,并且为两个领域找到或界定相对应的规则或德目(“私德”与“公德”)。
本文尝试基于胡塞尔的身体理论,从身体经验出发对身体的导向性空间做出进一步划分,从而说明身体空间的圈层结构。
来源|现代哲学杂志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