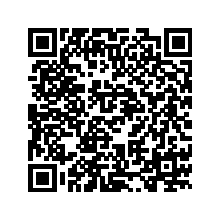学术资讯|我系蔡祥元教授发表文章:现象学与感性学的显现观比较——以张祥龙与泽尔的美学观为例

【关键词】显现;
【作者简介】

蔡祥元,浙江衢州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刊载于《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2期《艺术学与审美文化》栏目。
泽尔的显现美学是当代德国代表性美学思想之一。
张祥龙在《现象本身的美》一文中对胡塞尔的显现观进行了重构,阐明了显现自身就是美的。
下面我们将首先简要勾勒胡塞尔是如何论述显现问题的,以及在其视野中显现跟美是何种关系;
胡塞尔现象学可称为“意识现象学”,其核心内容在于揭示出意识具有一个意向性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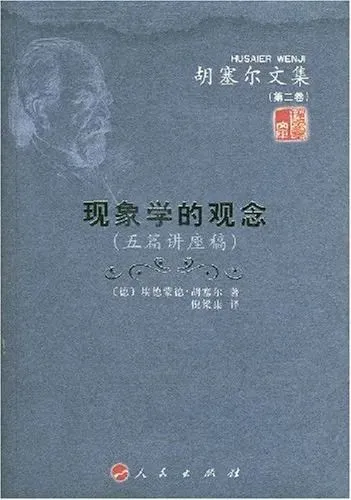
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人民出版社,2007年
胡塞尔注意到,“显现”(Erscheinung)在日常语言中有多重意思。
下面我们简要考察一下在胡塞尔现象学语境下显现与美的可能关系。
根据以上有关意识行为的奠基关系,不难看出,在胡塞尔这里,审美感知不同于一般的感知活动,它们是本质上两种不同种类的感知。
美的感受或美的感觉并不“从属于”作为物理实在、作为物理原因的风景,而是在与此有关的行为意识中从属于作为这样或那样显现着的、也可能是这样或那样被判断的、或令人回想起这个或那个东西等等之类的风景;
相对来说,胡塞尔在一封书信中倒是更为集中地论述了艺术直观(也即审美感知)与现象学直观的可能关系。
艺术家与哲学家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前者的目的不是为了论证和在概念中把握这个世界现象的“意义”,而是在于直觉地占有这个现象,以便从中为美学的创造性刻划收集丰富的形象和材料。
由此,我们可以简要总结胡塞尔对于审美感知的基本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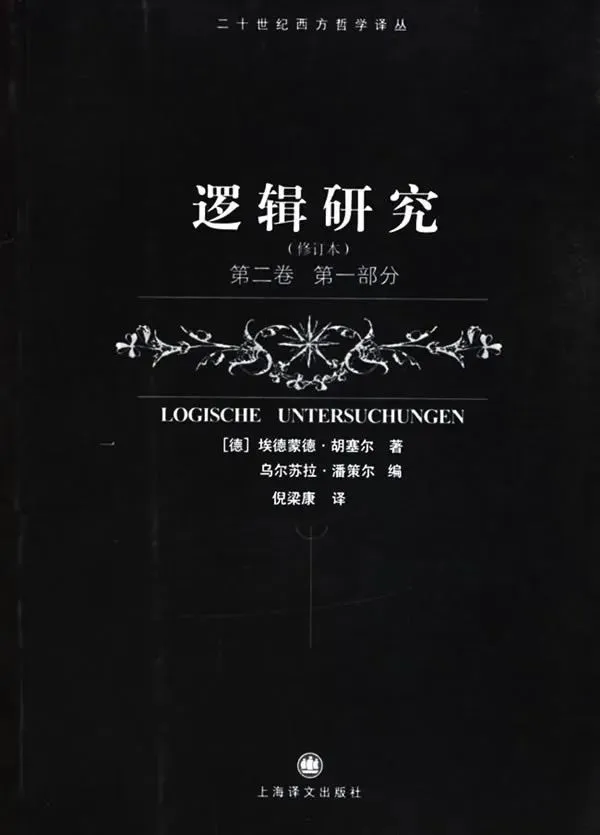
胡塞尔:《逻辑研究》,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
按胡塞尔的思路,对审美现象的进一步分析将会转向对审美意向性行为与意向相关项的考察。
张祥龙在《现象本身的美》这篇文章中提供了一个他的现象学美学观。
那么,张祥龙是在什么意义上说纯现象就是美的?
一方面,他对美感经验进行了分析,阐明它具有现象学的“现象”意谓。
另一方面,他从现象学的“现象”分析入手,表明原本的现象都是美之显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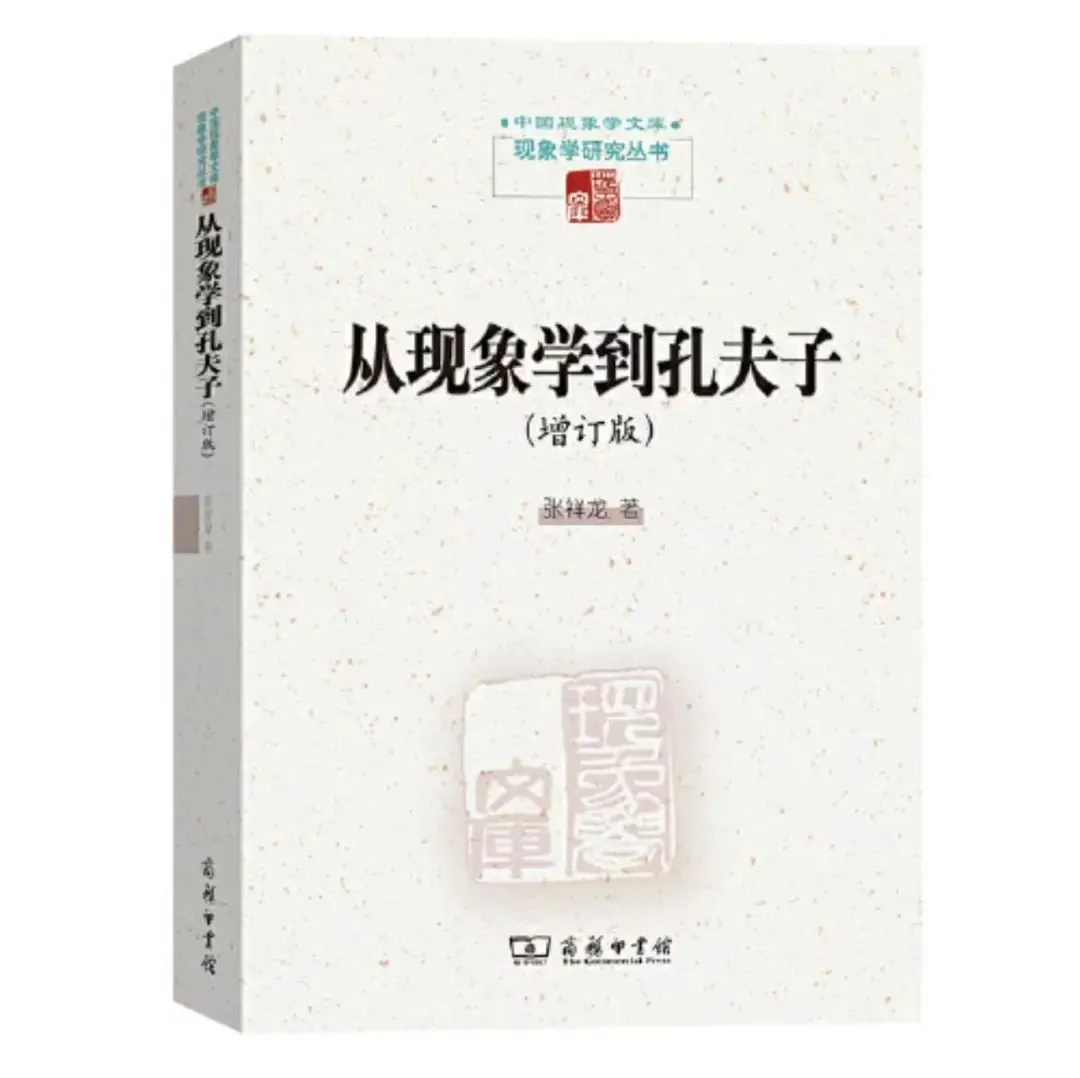
张祥龙:《从现象学到孔夫子》,商务印书馆,2011年
但是,如果只是给出意向行为与意向对象的相关性,那不过是重述胡塞尔的意向性理论,无法直接构成对美的阐发,毕竟这只是一般意识行为的基本构造而已。
为了进一步论证一般的现象之显现就是美,张祥龙结合胡塞尔后期的发生现象学思想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将胡塞尔前期相对静态的意向性构成思路扩展成“境域构成”思想。
也正是在这种境域构成的视野中,美学问题或美的现象有了更多的阐发空间,比如海德格尔后期就将存在问题与艺术现象关联起来思考。
这种纯现象在纯直观中原发地构成,完全不涉及任何再造式的联想、存在设定和概念把捉。
因此,现象之美,对于张祥龙而言,乃是此种境域中的纯构成之美。
其实现象学讲的现象本身就包含着这种引发距离或自由空间。
但是,在日常经验中,我们对事物的感知并不就是美的。
由此,张祥龙对胡塞尔现象学中的显现观进行了一个美学改造,并且认为借助现象学的构成观(相比朱光潜的美学思想)能够更好地说明美本身是如何出现的。
与张祥龙借助现象学视野阐发显现之美不同,泽尔的显现美学接续的是鲍姆加登的感性学思想,可以说是在美学传统中深化了美学的基本问题。
但是,日常生活中的感知经验并不都是美的。
在考察一般感知与审美感知的区别之前,泽尔又区分了一般感知的两个不同含义。
为了更好地阐明两者的区别,泽尔在感知对象的基础上提出了“显象”(Erscheinung)的概念。
审美感知的出发点也是显象(这是它有别于知觉性感知的地方),但它不是把显象把握为“实际”(Sosein),而是着眼于显象的“游戏状态”来把握它,这种把握就是显象的“显现”(Erscheine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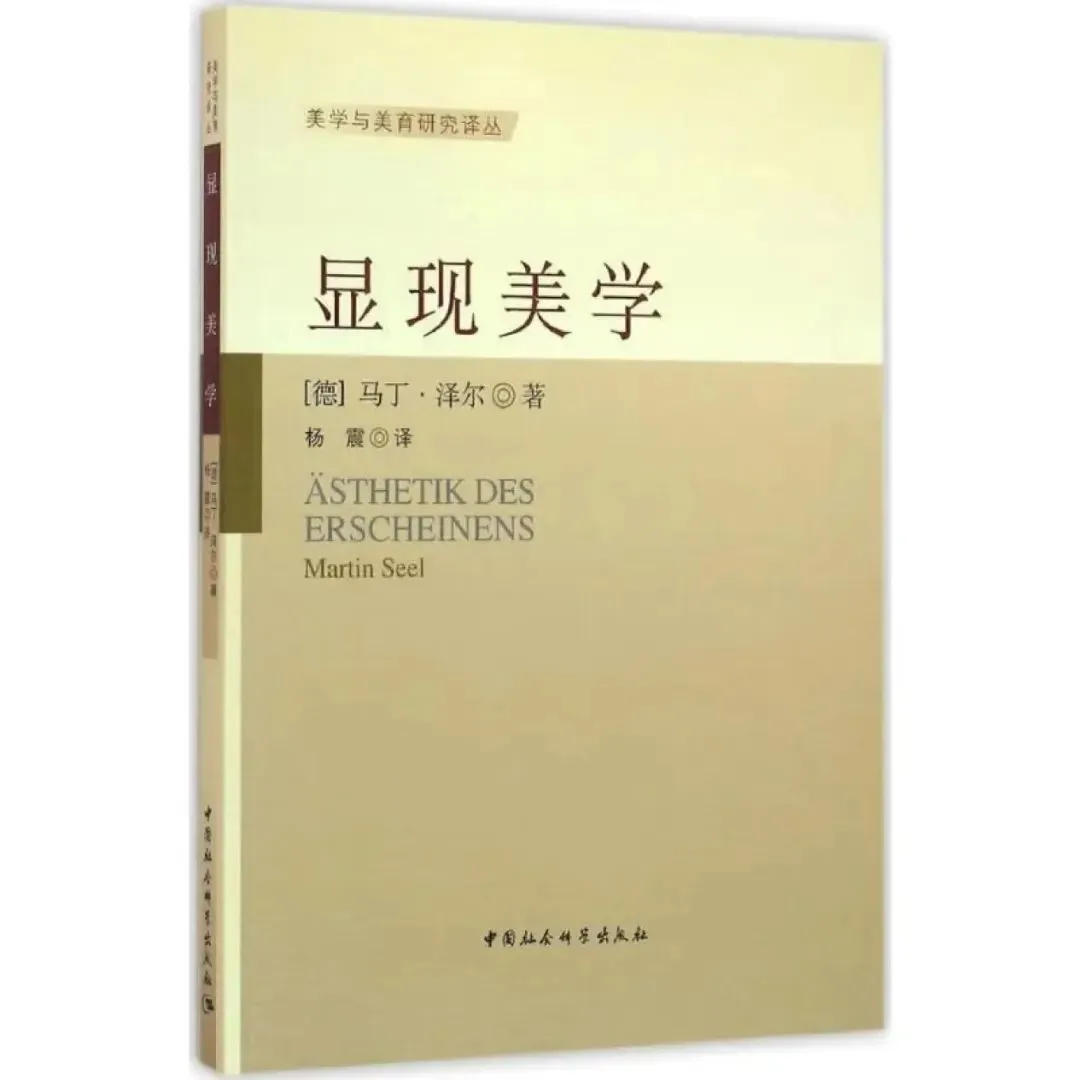
泽尔:《显现美学》,杨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
泽尔还根据时间性特征对显象的上述两种不同的出场方式作了区别。
因此,泽尔的显现概念跟一种独特的当下的时间维度密切相关。
泽尔有关显现美学的阐释虽然是在感性学的视角下展开的,但是,他对经验性感知的辩驳、对显现的时间性的阐发都与现象学视域下的显现有着某种关联。
张祥龙的现象学美学观接续自胡塞尔现象学,且更为集中地考察了显现与美感体验的内在关系,因而其与泽尔的显现美学有着同样甚至更多的相通之处。
令人遗憾的是,泽尔在论证其显现观的时候诉诸了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甚至诉诸了分析哲学传统也即麦克道尔的知觉观,却有意回避了胡塞尔的现象学,所以我们不能通过泽尔自身的论述来具体分析他与胡塞尔现象学的思想关联与差异。
首先,双方对显现机制的刻画不同。
其次,双方在对显现的时间性特征的阐发上也有根本区别。
在笔者看来,以上论及的两个主要的差别也可能构成了泽尔感性学的某些不足。
前文指出,泽尔的“境象的游戏”有赖于境象本身的“出场”,而境象的出场有赖于“概念”。
再一个就是时间性问题。
(本文部分图片来自网络,仅用作学术交流。
来源 | 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初审|韩 珩
审核|卢 毅
审核发布|屈琼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