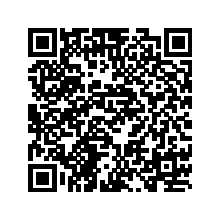学术资讯 | 卢毅:《家的无意识结构与主体化功能——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家情结》
《家的无意识结构与主体化功能
——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家情结》
文 | 卢毅
原文载于《哲学分析》2022年第1期

卢毅,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笛卡尔与法国研究中心负责人。研究方向包括法国哲学、精神分析、哲学心理学、伦理学、社会与文化哲学、马克思主义与左翼思潮等。在《哲学研究》、《世界哲学》、《哲学动态》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十余篇,译有《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雅克·拉康研讨班七: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商务印书馆,2021年)等。
摘要:不同于存在主义将人构想为被抛入世的孤独存在者,精神分析从一开始便将人置于家中进行考察,认为人在根本上便是有家、在家且恋家之人。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家首先是作为家族世代传递的无意识结构,具有赋予每个主体以其独特身份与位置的重要功能,是人由个体转化为主体的首要场域。作为主体的人往往不仅生于且终于、困于也成于作为一种情结的家中,而且正是对这种家情结的升华,造就了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使得"国"在文化无意识层面有可能成为"家"之命运、结构与功能的延续、拓展与深化。
关键词:家; 无意识; 情结; 主体; 精神分析
一、引言:精神分析视角下的家——有家、在家与恋家
存在主义自其思想先驱克尔凯郭尔,至其代表人物海德格尔与萨特,都将人构想为本质上是被抛入世的孤独存在者。例如,在海德格尔看来,作为“此在”之人在根本上乃是无家可归的(unheimlich)或具有某种无家可归性(Unheimlichkeit)。这种无根性或无家性虽赋予人“向死而在”的本真可能性,却也使人之在世存在注定饱受焦虑或“畏”(Angst)之无尽困扰。跳出这种存在主义的立场来看,海德格尔对人的所谓存在之基本境况的上述刻画,或许更适合被视为对“上帝之死”后身处存在论困境中的现代(西方)人之“虚无主义”处境的写照,而似乎不足以构成对一般性的人之本然或实然存在状态的揭示。
与强调人之无家可归与孤独自由的存在主义不同,精神分析自弗洛伊德开始便将人置于家中进行考察,认为人在根本上便是有家、在家且恋家之人,强调家对人之不可或缺的奠基性与构成作用。精神分析并未从存在主义仍未彻底摆脱的哲学玄思出发,而是从其日常的临床考察与实践经验出发,发现现实中的人首先是有家之人。具体而言,现实中的人并非从虚无中被抛入世界,而是通过家诞生于世,是家族和家庭的成员与“产物”——这既体现在家族身份世代的符号性传递层面上,也体现在家庭双亲通过结合而生育后代的身体实在层面上,因此不可避免会带有家的烙印。如此一来,作为有家之人,人既非绝对孤独,亦非绝对自由,而是在享有家的养育、呵护与陪伴的同时,也肩负着对家的责任。由此视角出发,精神分析所关注的(现代)人的各种心理症状,亦可被视为“人—家”关系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失调或紊乱。
人不仅有家,而且在家。具体而言,人往往是先在家中——即家的场域、关系 与氛围中——出生和成长,而后才离家,并成(立新)家,如此代代相承、绵延不 绝。因此,就人的整体生命状态或存在样态而言,在家既是一种本然的真态,也是 一种实然的常态。与之相应,从一种“家本位”的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视角出 发,心理症状作为人非本真的或病理性的存在状态的显现,既可能与人在存在论层 面是否真正“在家”的状态有关,也可能要进一步追究到人在家中是否有其应有位 置的问题上。此外,除特殊情况(如忤逆家长、有辱家门或家人尽逝等)外,人在 家中长成并离家之后,始终还有(原来的)家可归,而非如经典存在主义所言,在根 本上被剥夺了归家的可能性。
同样就人的本然与实然存在状态而言,归家不仅是一种通常不会被剥夺的可能 性,也是一种深层心理情结之持存与效应的必然体现。家作为人首要的生存场域, 不仅为人带来了各种源初的人性体验(如恻隐、羞恶、恭敬、是非),培育了其真正 人性的基础(如仁、义、礼、智),也因此在人的精神结构中留下了一种难以磨灭的 眷恋印记,注定了原本就有家之人在家中长成后依然恋家的本真情态。怀乡与归家 作为人生漂泊在世的心之所系,亦是对这种本真依恋情态的印证。然而,尽管人本 性恋家,却不可放任这种留恋自行其是,而须对其加以引导和教化,否则同样会由于对某种幼稚恋家心态的原始固着,而使人的发展陷入停滞并引发各种症状。
就其本然状态而言有家且在家之人,其在无意识层面对家的这种深刻认同与深切依恋,可以说构成了“家情结”的核心,由此也确保了家的无意识结构及其主体 化功能的有效运转。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出发,家首先不是一种有形的社会结构,而 是一种在拉康所说的以语言能指为载体的“符号性的”(symbolique)层面无形地传 承着家族世代命运——包括幸运、厄运、荣誉、罪行、欲望、创伤、症状等——的无意识结构。这种无意识结构因其兼具世代性与同步性可被视为一种具有历史性/历时性的共时性结构,同时也始终蕴含着被重构与改写的可能。作为这种无意识结 构的家,也因其具有赋予每个主体以其独特身份与位置的重要功能,而成为人在一 般情况下由个体转化为主体的首要场域——每个人通常首先是在其家的独特处境 中,在对家所代表的价值规范与伦理规则的独特认同中,在对家所承担的独特责任中,开始生成一个真正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主体。最终,正如弗洛伊德所表明的,是对冲动(Trieb)的升华而非直接满足才造就了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同样也可以 认为,正是凭借对家情结的升华而非原始固着,才筑就了诸如“国家”这样的政治 命运共同体,以及人们投身于其中乃至为其献身的政治热情,使得“国”在文化无 意识层面有可能成为“家”之命运、结构与功能的延续、拓展与深化,亦即作为一种 “家国情结”对人类主体的伦理与政治行动发挥至关重要的导向与推动作用。
二、家的无意识结构:命运、传递与重构
如前所述,在精神分析的视角下,家首先是作为一种无意识结构得到考察的, 并且这种结构不应仅限于传统精神分析往往首要关注的“父亲—母亲—孩子”的俄 狄浦斯式三元结构,而是同样也该包括更具历史性的家族代际传递结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理由将前者视为后者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尽管从弗洛伊德到拉康, 精神分析始终都强调家的无意识结构对主体之个性与命运的重要影响,但无论弗洛伊德还是拉康,均未将这种影响视为纯粹单向的或严格决定性的——否则,人们接受精神分析治疗以求深入改变的可能性便不复存在,精神分析作为一种实践而存在 的意义也就相当有限。恰恰相反,对人性洞察精微的精神分析,始终为一种反向影响留下了余地,为在家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主体保留了回过头来重构家的结构本身的可能性,因此也使得对人们通常诟病精神分析的所谓“精神决定论”进行反思与澄清成为必要。
家的无意识结构对于家族命运的传递看似神秘莫测,实则有理可循。此处试以 希腊传说中的安提戈涅及其家族命运为例略加说明。在索福克勒斯笔下,安提戈涅所面对的正是传递到她这一代人的诅咒与命运,而拉康甚至将这种受到诅咒的 家族命运解读为一种“冤孽”(μέριμνα)。有必要强调的是,这种命运或“冤孽”的 传递并非当事人有意为之,而恰恰是凭借语言的诅咒而得以无意识地实现。安提戈涅义无反顾去埋葬的那位亡兄,正是死于得知事情真相后自毁双目并遭放逐的父 亲俄狄浦斯的亲口诅咒。因此,安提戈涅的行动所承担的并非其兄意外身亡的结局,而是其家族已然注定的悲剧命运。不仅如此,俄狄浦斯本人的结局同样可被视 为其家族命运的无意识传递使然,而这一结局早在其父拉伊俄斯年轻时遭受佩罗普斯因丧子之痛而发出的诅咒中便被预先决定。若继续向前回溯,便会发现整个忒拜王室的“冤孽”或悲剧命运,甚至可以一直追溯至第一代国王即忒拜城的建立者卡 德摩斯之孙彭透斯(也是第二代忒拜国王)冒犯酒神而遭诛杀一事。此后,每位国王都在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中短寿促命或不得善终,一直通过以语言为中介的遗命 与诅咒传递到第七代国王俄狄浦斯,并继续殃及他为争夺王位而同归于尽的两个儿子以及看似渔翁得利的克瑞翁。安提戈涅之于整个家族命运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她 实际上是真正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是真正意义上的悲剧英雄,因为她看出除非自己 主动去承担波吕尼刻斯身上所承载的整个家族世代积累下来的冤孽,否则事情依 然难得善终。正是安提戈涅出于完全的自由决断并凭借一己之力重构了家的无 意识结构,中止并扭转了家族厄运的延续,使得整个家族的命运有了转入新轨道的可能。
此处便涉及家的结构规定性与人的自由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在精神分析 看来,尤其是从拉康的立场出发,家作为一种无意识结构,其相对于每一个体而言 具有先在性、奠基性与构成性。每一个体在正式诞生于世前,便已经在作为一种无 意识结构的家中被欲求、期待、谈论或厌弃、憎恶、诅咒等。就此而言,每一个体 都可被视为家的命运、话语、荣誉、欲望、创伤、罪行等维度的载体与产物,因此不 可避免地会带有家的烙印乃至“症状”。一般情况下,家会给新到来的个体一个位 置——尽管这个位置可能并不一定合适,并且会促使其以特定的方式将家既有的结 构继续传递下去,而个体起初更多只能接受这种规定与要求。此阶段大致对应于拉 康谈论主体化过程问题时所说的“异化”(aliénation),个体只有放弃其最初任性的意 愿并选择接受家所代表的伦理法则和社会规则,日后才可能获得一个真正得到社会承认的主体地位。
不过,随着其成长与主体性的发展,个体或将开始不满足于全然服从家的结 构规定性,而试图与家所代表的符号性的“大他者”(Autre)的要求与欲望拉开距离——这大致对应于拉康所说的“分离”(séparation),并开始注重于探索自身欲望 的原因。此时的个体看似收回了至少一部分自主权,却往往在不知不觉间依然受制 于朝向另类他者(如离经叛道者、标新立异者)的无意识幻想,而仍不足以被称为 严格意义上充分自决的“主体”。不仅如此,这种处境下的个体往往还会在有家与 无家、在家与离家、恋家与厌家之间陷入冲突与挣扎,并由此产生各种病理性的症 状。更极端地,即便个体决意通过背离家门并自觉承担其后果的方式来凸显其个性 与自由,并由此符合拉康所说的按其欲望行动的伦理主体的标准,但家与人之间 具有创伤性的张力关系依然存在甚至加剧,因此很难说是对此问题最理想的解决 之道。
最理想的解决之道应当是能兼顾二者,而这并非乍看上去那样不可思议。结合拉康对安提戈涅处境的独到分析,以及他对弗洛伊德“它曾在处,我应生成”(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这一伦理箴言的创造性解读,有理由认为:真正自觉地去 以个体自己欲望的独特方式为家这一先我而在的“它”揽责 ,使“我”之充分自决 的伦理主体性得以在真正彰显的同时,也使得促成家的传承与兴盛、实现家与人之 相互成就与共同完善成为可能。相反,无论是完全被动地接受家族命运的安排,还 是自以为是地离家出走或与之决裂,个体或始终仍不自觉地受制于家里家外的“他者”或“它者”,或难以兼顾孕育了“我”也等待“我”去继承的“它”与“它”所养 成也试图走出“它”的“我”。通过在家族命运与个体欲望之间找到甚至创造出 一个有机的连结点,以此实现家的结构规定性与人的自由主体性的辩证综合,完 成对家与人都具有积极意义的双重重构,或许才是彻底“穿越幻想”(traversée du fantasme)——既穿越命运之绝对必然的幻想,也穿越个人之绝对自由的幻想—— 的通透境界。
三、家的主体化功能:认同、责任与生成
前文在探讨家的无意识结构的过程中,已经涉及对家的主体化功能的揭示。实 际上,作为无意识结构的家,无论是其运转还是其传承,在根本上都离不开家中的 主体,而家中的主体虽然同样是家的产物和载体,但也更应该成为真正意义上家的 “主体”。起初由家所孕育并养成的人,后来将为家担负起责任;起初由结构所奠基并构成的主体,后来将承载结构的过去与未来。由此可见,家与人、结构与主体之间其实存在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倘若少了家的结构,人将难以成其为主体;倘若少了作为主体的人,家的结构也将难以为继。家的结构完全缺失或其中的主体彻底缺席,这些情况在现实中是相当罕见的。即便在大多数的“非正常”情况下,有缺陷的家庭或家族结构同样少不了成问题的主体(暴力或懦弱的男性、抑郁或焦虑 的女性等)的参与或配合,并且往往也会产生新一代的主体来延续——当然也可能是扭转——家庭乃至家族的结构与症状。
在家的无意识结构的传递或重构以及家中的主体生成并扮演某种角色的过程中,作为一种无意识心理机制的认同(Identifizierung)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且 体现出了不止一种向度。首先,认同可以表现为对家中特定主体或其角色的认同。这种认同既可以是通常被社会所接受的(如弗洛伊德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的“正面 形式”时所说的男孩对父亲的认同、女孩对母亲的认同),也可以是不太被社会所接 受却仍普遍存在的(如弗洛伊德在讨论俄狄浦斯情结的“反面形式”时所说的男孩 对母亲的认同、女孩对父亲的认同)。在此问题上,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发 现并强调:即便是在前一种情况下,认同依然是受到限制的,男孩无论如何认同父 亲,女孩无论多么认同母亲,他们都不能在一切方面(尤其是不能在性方面)将自 己完全置于父母的位置上,否则便有乱伦之虞。由此可见,在以家的结构为基础所 展开的常规主体化过程中,认同从一开始便伴随着压抑(Verdrängung),因此在本质 上可被视为一种蕴含差异的同一化过程。
认同也可以表现为对家的既有结构的认同,包括对前文所述的家族命运的认 同,也包括对特定类型的家庭或家族关系的认同。在这种认同中,个体的主体化一 般体现在对家结构的延续与传承上。就现实情况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言,个体往往会 不自觉地让自己成为家族的厄运、创伤与症状的载体,并且无意识地选择参与到让家的问题处境延续下去,甚至不断恶化的力量中去。换言之,在这种情况下,个体通过对家的无意识结构的“症状性认同”,扮演了作为症状主体将家的症状结构延续和传递下去的角色,对家的命运本身的由来与去向则缺乏关照。这种认同所产生 的主体只能是拉康意义上病理性的症状主体——可按照神经症、性倒错与精神病等 不同的临床结构再进一步划分——或“被划杠的主体”,而有别于严格意义上充分 自决并能够承担起一种真正责任的主体,亦即能对个人与家族命运进行积极重构的伦理主体。
认同的第三个向度,表现为对家的本真使命的认同。到此,个体既非单纯认同 家人的角色,亦非仅仅认同家族的命运,而更是认同光耀家门并使之薪火相传的使 命。尽管这一使命的完成少不了对家人先辈的学习与效仿,也离不开对家族命运的 了解与接纳,但更重要的是伦理主体性的觉醒与彰显,亦即个体觉悟到自己也可以 像安提戈涅那样,凭借完全出于自由决断且具有深刻伦理价值的内在欲望,去尽其 所能地承担家的结构与命运,并在更积极的方向上对其进行重构与改写,以使其得 以代代延续且蒸蒸日上。正是在为这先于“我”而为“我”奠基的家无条件揽责的 过程中,正是在对根本上是期待“我”使其世代延续并发扬光大的家的积极重建中, 正是在面对家时“我欲成其善”的本真态度中,一个作为真正意义上伦理主体的 “我”,才得以从此前“无主体的”或“症状主体的”状态中生成。由此而生的这个 “我”并非无家之人或家中的不速之客,而恰恰是原本就有家、在家且恋家之人的主 体化形态,因此对家的揽责与成全,也正是对作为家中主体(或更确切地说是家之 “主体”)的人自身的实现与成就。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家的上述认同中,家的结构在发挥其主体化功能、赋予人 以主体性的同时,也赋予其个性和独特性。各家的处境都有独特性,各家背后所代 表的观念和规则也不尽相同,各家对其不同成员的要求和期许也有所差异。与之相 应,各人通常首先是在家的独特处境中,在对家所代表的价值观念与处世规则的独 特认同中,在对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所承担的独特责任中,而得以开始作为一个 真正具有独特个性的主体生成。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无意识结构或“情结”的家, 虽然无法完全代表整个社会或世界的结构,但作为个人主体化的首要场域,它不仅 在主体那里留下了源初的结构性印记,而且对主体而言也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一切 社会结构的“原型”,并在作为一种政治结构的“国家”中实现了自身的延续、拓展与升华。
四、结语:
家(国)情结——对性情结与代情结的整合及超越
弗洛伊德早在 20 世纪初的《论爱情生活最普遍的降格》等文本中便表明了这 样一种立场:正是禁忌与压抑的存在,才使得人类不再只是容易满足和容易空虚的 动物,而是造就了爱情令人心驰神往的魅力,并且为人类文明积蓄了创造与升华的能量以及发展与前进的动力。换言之,在弗洛伊德看来,正是对以俄狄浦斯情结 为核心的被压抑的无意识内容的升华,尤其是对这些内容的“去性化”操作,才造就了人类光辉灿烂的文明与文化——尽管这种即便身为精英也只能部分实现的升华,在相当程度上仍不免以各种心理疾病的广泛流行倾向为代价。
不满于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传统精神分析对俄狄浦斯情结或曰“性情结”的片 面强调,霍大同先生在国内精神分析学界率先提出了“代情结”的概念,以凸显家 结构的代际传承这一重要维度。然而,以上两种情结之间的关系很可能并非乍看 上去那样形成了某种简单的对立或互补。霍大同先生眼中以俄狄浦斯情结为典型的性情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亦可被纳入代情结的结构中。正如家的代际传承在现 实中必须借助性的结合才能得以实现,代情结本身的传递在结构上亦免不了性情结 的介入与承载。换言之,纵向的代际关系与横向的两性关系只是出于理论分析的目 的而被加以区分,实际上却不可截然相剥离,而是形成了一种更复杂的交织即“家 情结”。不仅如此,倘若从对俄狄浦斯情结本身的深入理解出发,同样也有理由质 疑将其化约为“性情结”的准确性与合理性——因为无论在弗洛伊德还是其后继者 那里,俄狄浦斯情结尽管侧重于凸显性的维度,但毕竟已经包含了代际传递与代际冲突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显然并不能被完全简化或归结为性的问题。
鉴于无论是“性情结”还是“代情结”的说法都各有侧重而难以全面反映精神 分析视角下家的问题的复杂性,“俄狄浦斯情结”的说法又意指含混而容易引起误 解,因此本文将通过提出“家情结”这一概念来尝试进行一种厘清与整合。如果说 弗洛伊德关于以俄狄浦斯情结为核心的被压抑无意识内容的升华理论依然成立,并 由此使人们得以在作为这一升华活动产物的人类文明(科学、宗教、艺术等)中找 到俄狄浦斯情结的各种痕迹,那么下文关于家情结及其升华简要的初步探讨,则旨 在从一个较为具体的维度出发,来聚焦分析作为一种政治共同体的国家,在何种意 义上可被视为“家”之命运、结构与功能在文化无意识层面上的延续、拓展与深化。
有家、在家与恋家,作为人之在世存在的本真状态,也意味着家情结的根深蒂固。就此而言,不难设想作为一个主体的人,往往生于也终于、困于也成于作为一 种情结的家中——生于作为主体化之首要场域的家中,也终于作为世代延续之基本 结构的家中;困于作为牵挂眷恋之源初开端的家中,也成于作为进德修业之根本始 基的家中。然而,正如《大学》所示,“齐家”并非人之修行的最高目标,而是可被 视为“治国”的准备与条件,并最终在“平天下”且“天下一家”(《礼记·礼运》)的 理想观念中完成自我扬弃,即获得更高层次的实现。实际上,正是凭借对家情结的 升华而非原始固着,才筑就了既超越了“家”又与之同构的“国家”这样的政治命运 共同体,以及人们投身于其中乃至为其献身的政治热情。换言之,正是凭借这种得 到升华的“家(国)情结”,人们得以走出狭义上的家,而走向广义上的家即国家乃 至“天下一家”。这种家国情结作为一种强大的文化与心理力量,将推动人们有可 能在家与国的冲突中通过选择为国尽忠而实现对为家尽孝的扬弃。可见,对家情结 的升华既不能够也不旨在使其彻底消失或瓦解,而毋宁说是对其命运之延续、对其结构之拓展以及对其功能之深化。
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来看,对家情结的这种升华,意味着将家情结从个体性的心 理无意识层面提升至集体性的文化无意识层面,并将个体性的、各为其家的家情结 整合或凝结为集体性的、天下一家的家国情结。尽管其中涉及的具体而复杂的运作 机制仍有待进一步探究,但至少可以明确的一点是:此处必然涉及与列维纳斯等人所强调的“他异化”路径相反的一种“亲近化”进程。由家而国的拓展进路,显然涉 及对某种源初他异性的亲近化,而这种亲近化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对他异性的同 化或至少是淡化。对此,既可以从当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出发斥之为同一性形而上学的暴力,也不妨从传统中国思想的直觉出发视之为亲亲之仁心的推展。然而细细想 来,国之作为政治共同体,正如家之作为生活共同体,其实从根本上并不否定或拒 斥个体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甚至还可以被理解为恰恰是要在一种亲近化的共有结构中以差异化的方式安顿、保障和实现个人独特的主体性。与之相应,一生系于家 (国)情结之人,亦将以其独一无二的个性化方式,与他人共同投身于一种命运共同 体的建构与重构中。
(责任编辑:韦海波)
参考文献
[1]参见Martin Heidegger,Sein und Zeit, Tübingen:Max Niemeyer Verlag, 1967, S. 188—189。
[2]具体而言,心理症状的典型受害者,往往最初是有家却不在家的被遗弃者或被托管者,以及家庭关系有严重缺陷或错位者,他们或是有家而无法在家中真正占据一个位置(如弃儿),或是其在家所占据的位置乃是一个有缺失的位置(如留守儿童、单亲儿童)或错乱的位置(如乱伦关系的受害者)。
[3]对精神分析语境下精神决定论或精神因果性与无意识的自由选择之间关系的探讨,可参见卢毅:《从病理学透视到生存论结构——论萨特与拉康学说中的疯狂与自由》,载《学术研究》2020年第3期。
[4]Jacques Lacan,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Seuil, 1986, p. 307.
[5]Ibid., p. 329.
[6]忒拜王室家族的命运虽未在安提戈涅慨然赴死后立即发生扭转,却无论如何正是凭借她对波吕尼刻斯合乎神意的安葬之举,才使得波吕尼刻斯之子忒耳珊能够登上王位并最终让忒拜走上复兴之路,由此仍可见安提戈涅之决定与行动对于改写整个家族命运走向的关键性。
[7]参见Jacques Lacan,Le Séminaire Livre VII: L’éthique de la psychanalyse, p. 362。
[8]Sigmund Freud,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in Gesammelte Werke XV, London:Imago, 1944, S. 86
[9]参见Jacques Lacan, “La chose freudienne”, in Écrits. Paris:Seuil, 1966, pp. 417—418。
[10]由此观之,《大学》所谓“欲齐其家者”,亦不妨被解读为“有齐家之欲者”,而“齐家之欲”作为一种显然具有伦理价值的欲望或曰“伦理欲望”,不仅与人们一般所理解的“食色之欲”等“自然欲望”拉开了距离,也为人们重新理解儒家的欲望观且尤其是“人欲”与“天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契机。
[11]家与人、它与我宜须兼顾、缺一不可的立场,与孙向晨教授在其近著《论家:个体与亲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中所提出的“个体”与“亲亲”作为现代人双重本体的观点——既坚持现代个体的自由,又尊重传统亲亲的价值——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处。
[12]此处涉及对拉康相关思想的借鉴与进一步发挥。而对拉康本人所构想的主体生成或主体化过程的三个环节(异化、分离与穿越幻想)及其中所蕴含的自由观的解读,可参见卢毅:《异化、分离与穿越幻想——论拉康学说中的自由观》,载《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4期。
[13]按照《精神分析词汇》的作者拉普朗什与彭塔利斯的基本界定:“[认同是指]主体同化他者的某个方面、某种属性、某种品质,并完全地或部分地以这个他者为模型发生转变。人格通过一系列认同而形成并分化”(J. Laplanche, J.-B. Pontalis,Vocabulaire de la psychanalyse, Paris:PUF, 1967, p. 187)。上述界定中出现的“他者”(l’aure)这一说法,尽管倾向于指代“他人”,但也不妨将其解读为拉康式的“他者”,由此便得以拓展并深化“认同”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主体”概念在精神分析语境下的内涵。按照这种拉康式的解读,在“家本位”的问题语境下,“他者”作为认同的目标或对象,既可以指家中具体的某人,也可指某人在家中所占据的位置、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功能等,还可指家或相关衍生机构的结构、关系、命运、使命等。与之相应,“认同”也得以体现出下文将要展开的几个向度,“主体”亦得以跳脱出“人格”这种心理学概念而跻身于存在论与伦理学范畴。
[14]参见Sigmund Freud, “Das Ich und das Es”, in Gesammelte Werke XIII, London:Imago, 1940, S. 259—262。
[15]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爱情心理学文选》,卢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xii页。
[16]参见霍大同:《代情结与中国人的无意识结构》,载《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1期。